扫描分享
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文/李舒豪,北京大学法学院2021级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证券市场中的借壳上市具有多重交易属性,但其核心在于控制权交易。具有中国特色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出台之初用于应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对实证法规则的考察表明,监管机构试图转变其定位,将其同时用于应对借壳上市中的控制权交易风险。分析借壳上市中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实际运行的直接、间接机制可知,其无法应对控制权交易的风险,甚至会向借壳方股东施加采用短视、违法经营行为的负面激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观察,业绩补偿承诺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既有监管规则和交易实践的一种延续。
关键词:业绩补偿承诺制度 借壳上市 控制权交易 制度错位 制度变迁
公司并购是公司法与证券法学界的“顶流话题”,这尤其体现在有关控制权市场、控制权溢价的研究中。[1]后来的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公司并购中的控制权溢价现象,并将其与法律理论中的股东平等、控股股东诚信义务(fiduciary duty)与少数股东(minority shareholder)保护等建立联系。对于刚刚“三十而立”[2]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尽管第一起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早在1993年9月就已出现,[3]且A股市场在经历2005年至2008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后具备了不再区别对待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全流通条件”,控制权交易数量呈逐年递增的态势,[4]但由于我国监管规则的限制[5]、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国有股份转让的严格限制,以及监管机构对于收购方的不友好态度[6]等多方面原因,我国控制权交易的绝对数量仍然相对较少。[7]
在我国难言活跃的控制权交易市场中,由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而受到企业青睐的借壳上市[8]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类控制权交易,甚至形成了核准制时代相当繁荣的控制权市场——“壳市场”[9]。借壳上市具有控制权交易和资产重组两层交易属性。对于其中的风险,拟上市公司作为借壳方,不仅是控制权交易中的买方,也同时构成并购交易中的被并购方。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监管要求,借壳方需要向上市公司出具强制性的业绩补偿承诺。这类“买方对赌”式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其他法域的实践中并不存在,[10]具有中国特色,其源起、机制和成效都亟待仔细评述。
然而,在中文学界,关注公司并购中控制权溢价问题的研究数量不多,[11]更遑论对借壳上市中控制权交易风险的讨论,以及对于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反思;[12]而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文献则恻重对经验性(empirical)证据的分析,缺乏与法学理论、法律制度的对话。本文将通过回答以下三组问题,尝试填补既有研究的不足:(1)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理论上能够发挥何种功能,以及其在实证法上具有何种定位;(2)其在借壳上市所形成的控制权交易市场中具体如何运转、是否能够应对控制权交易的风险;(3)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如何理解我国监管者在借壳上市中运用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选择?
借壳亚夏汽车上市的中公教育在业绩承诺期满后旋即爆雷的案例为本文的观察提供了绝佳的市场实践样本,而控制权溢价、控股股东诚信义务、资产重组与信息不对称、制度的路径依赖等则是深入分析的理论支撑。目光往返于真实案例与理论之间,本文前三部分试图评估业绩补偿承诺制度适用于借壳上市中的正当性和实际绩效,第四部分则以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中国特色”为引,归纳我国资本市场各类监管规则、交易实践的共通特征,为监管者将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强制用于借壳上市的选择提供一个制度层面的初步解释。
一、借壳上市的交易结构、属性与风险
(一)概念界定与交易结构:中公教育借壳上市的实例
“借壳上市”在官方表述中的实质界定体现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而从描述性(descriptive)的角度,可以将“借壳上市”定义为在借壳方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进行、以资产重组和反向收购的形式展开、以获取“壳资源”为目标的控制权交易。借壳上市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借壳上市的目的是借壳方股东[13]收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14],但并不在于获得上市公司的资产、财务资源等,而是在于在我国IPO准入较为严格的核准制时代较为稀缺的上市公司“壳资源”;[15]第二,借壳上市实践中,获取控制权的方式由资产置换、股份转让、资产出售等多个步骤共同构成,区别于协议转让、间接收购、二级市场收购、要约收购、认购新股等各类传统的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手段;第三,借壳上市中,上市公司与借壳方股东进行的资产重组满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对借壳上市规定的“100%及以上”[16]财务指标或其他“根本变化”的标准。
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官方表述中的界定体现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即在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或进行其他资产交易行为构成“重大资产重组”[17]时,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手方应与上市公司约定交易所涉资产的预测盈利并签订补偿协议,在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盈利数时,依据协议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外,另有两部规范文件与其相关。[18]坊间往往将该制度称为上市公司的业绩“对赌”[19]。但应当注意的是,借壳上市中的业绩补偿承诺由购买壳资源的借壳方出具,这不同于《九民纪要》第2条所强调的PE/VC投资过程中“对赌协议”的“卖方对赌”安排,[20]而更接近于一种“买方对赌”的安排。
中公教育的案例能够清晰地展现借壳上市的交易结构与业绩补偿承诺的内容。中公教育于2018年以185亿元的价格,通过资产置换、发行股份与现金收购等多种方式借壳亚夏汽车上市,中公教育创始人李永新等8人签订了3年合计38.8亿元利润承诺的业绩补偿协议。然而,中公教育近况并不十分乐观。按照中公教育在2022年4月底公布年度报告的信息,其在2021年度的营收相较2020年下滑38.30%至69.12亿元,净利润则相较于2020年盈利23.04亿元的成绩下滑202.83%,最终亏损23.70亿元。[21]事实上,自2021年10月以来,中公教育便麻烦缠身,遭到来自交易所[22]和证监会[23]的关注、问询和调查。
中公教育在完成“三年之约”后的第一个年头便出现业绩滑坡,是本文选择中公教育借壳亚夏汽车上市作为交易实例进行讨论的主要原因。这一案例不仅具备借壳上市、业绩补偿承诺等要素,且中公教育采用的“协议班”模式尽管使其完成了快速的规模扩张,但高昂“合同负债”也受到了大量的质疑,其在承诺期满后即蹊跷地宣布营收下滑、利润暴跌,[24]正契合于本文试图论证的主张: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借壳上市中无法发挥效果,甚至存在不利于上市公司长期绩效和股东福利的负面后果。本部分将结合中公教育与亚夏汽车在2018年进行借壳上市交易时披露的信息刻画其交易结构,[25]并作为后续讨论的实例参考。
中公教育借壳亚夏汽车上市共分为三个交易步骤。首先是重大资产置换,亚夏汽车将除保留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李永新等11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中公教育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前者作价133503.36万元,后者作价为1850000.00万元。[26]其次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第一步重大资产置换中,拟置入的中公教育100%股权这一资产与拟置出的亚夏汽车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为1716496.64万元,该部分由亚夏汽车以发行股份的方式从中公教育全体股东处购买;其中,发行股份的价格为3.68元/股(亚夏汽车的分红计划全部实施后为3.2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发行股份数量为4689881528股(亚夏汽车的分红计划全部实施后调整为5347063429股)。最后是股份转让,亚夏汽车的控股股东亚夏实业向中公合伙和李永新分别转让持有的80000000股和72696561股亚夏汽车股票,前者由中公合伙受让,对价为亚夏汽车置出的资产;后者由李永新受让,对价为100000.00万元现金。因此,整个三步骤的交易其实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中公教育股东与亚夏汽车之间的资产置换、发行新股交易;第二大部分是中公教育股东与亚夏汽车的控股股东亚夏实业之间的股份转让交易。
在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亚夏汽车置入了中公教育100%的股权,亚夏汽车的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变更为鲁忠芳、李永新,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李永新和鲁忠芳;亚夏汽车原控股股东亚夏实业获取了除保留资产之外的全部亚夏汽车资产,不再持有上市公司亚夏汽车股份。由此,中公教育完成了借壳亚夏汽车上市登陆深交所的交易。
此外,在中公教育的借壳上市交易中,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安排。第一,亚夏汽车与李永新等8名业绩补偿义务人于2018年5月4日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补偿期为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中公教育在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93000.00万元、130000.00万元和165000.00万元。第二,交易中存在对亚夏汽车股份的不同定价。[27]李永新等中公教育股东在以中公教育100%的股权为对价获取亚夏汽车发行新股和亚夏汽车资产的过程中,对亚夏汽车股份的定价为3.27元/股;而在以亚夏汽车的资产和10亿元现金为对价获取亚夏实业所持亚夏汽车股份的过程中,定价分别为12.69元/股(亚夏实业向中公合伙转让)、13.76元/股(亚夏实业向李永新转让)。
(二)多重交易属性与风险:以控制权交易为核心
从中公教育借壳亚夏汽车上市的交易结构可知,在规范(normative)层面,标准的借壳上市交易结构至少构成两个不同的交易类型,[28]一是上市公司的并购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二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
上市公司的并购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是上市公司作为交易主体,向交易相对方购买资产的行为,主要由《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进行调整。其风险主要体现在购买资产的溢价过高,可能导致后续的大幅商誉减值;[29]若资产重组同时属于关联交易,则向资产赋予高溢价可能成为购买方上市公司向关联方的利益输送(tunneling), [30]越发增加资产定价中出现不合理高溢价的可能性。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则更恻重交易双方以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作为标的而设计展开的交易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现代公司法中区别于一般财产组合的、“作为客体的上市公司”[31]的观念,主要由《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进行调整。控制权交易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原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权在交易中获取过高的溢价,尽管溢价在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分配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争议;[32](2)原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排挤(squeeze out)行为、单独出售公司职位的行为(sale of corporate office),以及新控股股东的不善经营、掠夺(looting)行为,也都会损害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利益。[33]
在形式上,对于兼具两种交易属性的借壳上市,其实际交易风险应同时来自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两个方面。然而,借壳上市交易结构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流行,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我国监管机构过度管制IPO状态下的公司上市融资诉求,[34]其实现的关键是借壳方股东能够获取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因此,借壳上市的主要交易目的在于完成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借壳方股东以此获取“壳资源”、使名下公司绕过IPO的常规程序而完成上市,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则以此获取现金或其他对价并退出上市公司。相较而言,资产重组不过是整体控制权交易的其中一个环节,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因此,借壳上市的核心交易风险实际上来源于其控制权交易的面向,如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获取不合理溢价后退出,以及新进入的借壳方股东滥用其控制权不善经营。就借壳上市的资产重组面向而言,由于此时交易的核心并非借壳方股东的资产,而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故上市公司购买借壳方股东资产支付溢价过高的风险逻辑已经发生转变:风险并不源于资产重组中上市公司作为买方相对于卖方资产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 [35]而是来源于原控股股东在出售上市公司控制权时与借壳方股东之间的博弈结果,甚至主要来源于双方的串谋。[36]此外,由于借壳上市的交易双方通常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几乎不存在利益输送风险。可以说,由于以控制权的转移作为主要交易目的,且控制权的转移会导致交易方获得或失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身份,改变各方在交易中的行为激励,因此传统上的资产重组风险不再具有单独讨论的必要性,借壳上市的主要风险依附于控制权交易中的各方博弈而产生,体现为控制权交易的风险。
二、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定位转变:实证法的考察
从证监会和上交所、深交所在监管借壳上市交易时可选用的规则来看,除基于《公司法》的程式(routine)控制和诚信义务[37],证券法规则体系内常见的核准制度或注册制度、信息披露规则、资格限制规则(包括收购方与财务人员),以及在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中相对特殊的要约收购、协议收购规则之外,本文所讨论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是监管机构介入借壳上市交易的“抓手”。然而,研究者在肯定监管机关通过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应对借壳上市风险的做法之前,至少应抱有如下疑问:业绩补偿承诺制度设计之初的定位如何?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回应的是借壳上市中的何种风险?
借鉴Roscoe Pound对于“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s)和“现实执行的法律”(law in action)的区分,[38]对制度如何运行的考察也应一分为二:一是制度设计的初衷或原意,即规则制定者对于其如何发挥作用的本来期待;二是制度在后续运行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机制及效果。[39]制度的实际运行可能是“歪打正着”的,因此有必要考察监管机构设立这一制度的原初动机及其变迁,避免对制度的目的、绩效形成错误的认知和评价,甚至形成观念上“将错就错”式的“坏均衡”。[40]
尽管根据证监会工作人员的考察,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早期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方案中也曾出现过类似业绩补偿承诺的条款,[41]但该制度的正式表达首次出现于2008年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42]且其在证监会颁布规则的实证法层面始终仅规定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各个版本中,从未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或其共同的上位法《证券法》中。那么,由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实证法规则中的分布可以推断,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设计初衷是用于处理资产重组问题中的风险,而并不涉及控制权交易这一面向。并且,从针对业绩补偿制度的学术讨论来看,在2008年正式写入规定之前,研究者就已指出这一制度主要用于应对资产并购中的高溢价支付、资产减值和商誉减值风险,[43]后续也有研究指出其用于保护公司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44]事实上,证监会工作人员的态度(尽管不能代表证监会的态度)也接近于此,“在重大资产重组中,被并购重组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成为业绩承诺协议产生的根源。就其初衷而言,是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并购重组交易的合理和公平”[45]。
在理论上,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对于标的资产状况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存在关联关系,是造成资产重组交易中溢价风险的主要原因。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应对资产重组风险的基本机制是通过对交易各方的激励进行调整,以控制信息不对称状态上市公司由于缺乏信息而“被动”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资产溢价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交易对方存在关联关系时上市公司因双方合谋而“主动”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资产溢价程度。
具体而言,由于交易对手方与上市公司签订了包括盈利预测数、补偿要求等内容在内的业绩补偿承诺,在事前,如果交易对手方利用信息不对称或关联方合谋推高资产定价,将盈利预测确定为不合理的数额,这将会带来较大的事后补偿可能性。交易对手方或关联双方出于对事后向上市公司进行高额补偿的厌恶,存在将资产定价向资产真实价值靠近的激励。这种机制设计其实与用于房产的“哈伯格税”(Harberger Tax)[46]有类似之处,即房产或土地权人的自我评估价格作为征税价格,权利人出于对高额纳税的厌恶,存在将房产或土地定价趋近于真实定价的激励。从另一个角度看,当资产市场上存在高度信息不对称时,交易对手方针对其资产的盈利预测资产重组交易中属于表明资产质量的“信号”(signal)[47],业绩补偿承诺机制则使补偿可能性、补偿金额与盈利预测挂钩,减弱了交易对手方发出错误信号的激励。而在事后,倘若资产存在较高的溢价,当与资产估值挂钩的盈利预测无法实现时,交易对方也会向上市公司进行兜底补偿,以此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尽管有研究者否定该制度应对资产重组交易风险的实际效果,[48]认为其无法降低控股股东与公众股东间的高昂代理成本(agency cost)[49]或财富转移效应[50],但也有相当多的会计学和管理学研究表明,[51]业绩补偿承诺能有效地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产溢价对上市公司及其公众股东带来的损害。
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在2014年进行了修订,这表明监管机构已经转变业绩补偿承诺的制度定位。2008年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并未区分应适用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资产重组交易范围,而在2014年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其第三十五条将上市公司收购非关联方资产且未导致控制权变更的交易排除在了强制业绩承诺的范围之外,交易各方可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且这一表述在2020年颁布的现行版本中得到了延续。[52]对此可以理解为,监管机构不认为有必要对上市公司的全部重大资产重组强制施加业绩补偿承诺制度,而仅在其存在关联关系,或导致控制权变更时才予以限制。
一方面,关联关系导致的利益输送风险本就属于资产重组交易的核心风险之一,按照前文的分析,业绩补偿承诺制度能够通过调整交易各方的激励,控制关联方合谋而导致的资产溢价程度,将该制度继续用于应对存在关联关系的资产重组交易,至少符合监管机构在2008年时制定业绩补偿承诺规则时的初衷。
另一方面,导致控制权变更的资产重组交易具有控制权交易的属性。控制权交易的风险不同于传统资产重组所关注的风险,其产生的原因并非是信息不对称或关联关系,而是控制权的独特价值,以及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等相较于公司中小股东拥有的巨大决策权力。相较于非关联交易式的资产重组交易,此类交易与其在交易属性、交易风险上的本质差异是涉及控制权交易,而与资产重组的面向无关。那么,监管机构对于非关联交易式资产重组交易允许交易方自主协商业绩补偿承诺,而针对涉及控制权变动的资产重组交易则强制推行业绩补偿承诺,应理解为对于后一类别中控制权交易风险的回应。[53]
此外,还需要澄清的是,监管实践常常将涉及控制权变更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同时认定为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54]似乎意味着,如果从资产重组的视角观察这类交易,其具有关联交易性质,强制推行业绩补偿承诺是为了回应关联交易伴随的利益输送风险。但本文认为,正是因为存在控制权交易,交易对手方才获得了潜在控股股东的地位,其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属性”来源是控制权交易,[55]交易双方因所谓“关联属性”产生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动机,如合谋、对抗性博弈等,应纳入控制权交易的整体框架下进行分析。在这类交易中,“关联属性”是形式上的结果,控制权交易才是实质上的原因。后者才是监管机构在此类交易中强制推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原因。
从对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实证法溯源可知,[56]其从2005年至2008年股权分置改革时期的“承诺”雏形进化而来,自2008年制度正式出台至2014年之前,业绩补偿承诺的定位是应对资产重组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输送风险,而在2014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完成修订后至今,监管机构对该制度采取原则自主协商、例外强制推行的态度。需要强制给出业绩补偿承诺的情形包括两类,应一分为二地进行看待:对于关联性资产重组交易,通过该制度防范利益输送的风险,并未偏离制度在最初出台时的定位;对于涉及控制权交易的资产重组交易,监管机构则试图转变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定位,将其用于应对其中的控制权交易风险。而站在借壳上市与业绩补偿承诺互动的角度观察规则的变化,借壳上市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语境下几乎可以与涉及控制权交易的资产重组画上等号:借壳上市在起初由于具备资产重组交易的规范属性而落入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调整范围,而在2014年之后,监管机构调整了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定位,强调其用于应对控制权交易风险,体现了对于借壳上市的针对性。
三、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借壳上市中的监管失败
在借壳上市交易中,被监管机构所仰赖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如何介入实际交易以应对控制权交易的风险,不妨通过中公教育借壳亚夏汽车上市的实例来进行考察。按照经济学中的理性人(rational person)假设,中公教育借壳亚夏汽车上市过程中的各方动机是:(1)亚夏汽车原控股股东亚夏实业的诉求是寻求高溢价售出其持有的控股股块(controlling block)并尽可能保留亚夏汽车的关键资产和“营业”(business);(2)中公教育作为借壳方,其股东的首要诉求是获取“壳资源”,即亚夏汽车的控制权,使中公教育尽快上市,具体方式则是要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取得尽可能多的亚夏汽车股份并持股达到“控制”水平;(3)亚夏汽车其他公众股东则希望新注入的中公教育资产有较好的盈利前景,但这一诉求的实现相对被动,因为其无法分享亚夏实业作为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溢价,也受限于表决权比例,无法直接影响中公教育与亚夏汽车的交易方案。
依托对于各方动机的描述,可以进一步将该起借壳上市的控制权交易刻画为三组利益冲突关系和一组利益趋同关系来加以理解。[57]其具体表现为:第一,亚夏实业与中公教育作为上市公司亚夏汽车控制权或所谓“壳资源”的买卖双方,在控制权对价的谈判上具有博弈关系。第二,控股股东亚夏实业由于在公司控制权转让过程中享有实际的决策权力(power),这使公众股东在控制权交易中的福利状况高度受制于控股股东,二者之间构成委托一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存在控股股东牺牲公众股东的利益以自渔的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58]尽管公司正常经营时也同样存在控股股东与公众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但其在控股股东即将退出公司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可以通过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的理论加以解释。在简化的有限次(finite)重复博弈模型中,当原控股股东仍在持续经营时,由于监管机构、公司机关和公众股东的监督机制,其与公众股东合作(cooperate)的效用高于其背叛(betray)公众股东以自渔的效用,而公众股东也自然乐见双方合作的结果,因此此时双方进行合作的策略选择互为最优反应(best response),双方的策略组合即构成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而当控股股东在控制权交易中决策时,这一有限次重复博弈进入最后一次,此时控股股东至少在交易完成后不再或不容易受到公司机关和公众股东的监督,因此无论公众股东选择合作还是发声(voice)等策略,背叛都是控股股东的严格占优策略(strictly dominant strategy)。[59]由此可知,在控制权交易中,原控股股东尤其可能牺牲公众股东的利益以获取更高额的控制权溢价等自我利益,大股东一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尤其严重。第三,中公教育的股东方(李永新、鲁忠芳)在获取上市公司亚夏汽车控制权后成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后,即使不考虑李永新担任董事长的事实,[60]李永新、鲁忠芳也已经持有绝对多数比例的股份,[61]能够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策略、业绩与股价表现,进而影响公众股东的福利情况,故其与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之间存在“大股东一小股东”或“董事一股东”的委托代理关系。这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问题在业绩补偿承诺的压力下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新进入的控股股东可能通过各种不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手段推高公司的短期利润,有损于中小股东利益。[62]第四,借壳上市中的利益趋同关系体现在,准备退出的原控股股东亚夏实业可能与借壳方中公教育的股东进行合谋,前者可以在股权转让交易中接受来自中公教育的控制权高溢价作为“贿赂”(bribe),利用其仍然代表亚夏汽车进行谈判的身份和权力推高估值,使中公教育获取尽可能多的亚夏汽车股份,而使中小股东的表决权比例大幅下降。[63]
前述四组利益冲突或利益趋同关系中,第一组利益冲突关系与交易双方有关资产的信息不对称有关,恻重于资产重组交易的面向。但交易双方在这组关系中的不同博弈姿态,如合谋、对抗等,会影响交易双方在其他几组利益关系中的激励,进而间接减小或放大控制权交易的风险。例如,原控股股东为了从借壳方股东处获取更多“贿赂”,与对方展开合谋,存在为推高借壳方资产定价、偏离上市公司公众股东利益的激励,借壳方股东也有进行相应配合的负向激励,更可能造成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股东利益的局面,可能放大控制权交易中的风险。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利益关系则对应在控制权交易中,原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高溢价、新控股股东经营不善导致公司和公众股东利益受损的风险。
根据前文分析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定位转变过程,在2014年完成规则修订后,监管方在借壳上市中强制推行业绩补偿承诺的主要目的正是应对控制权交易的风险。但对其实际运行的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进行的考察表明,我们并不能对此抱有过高期待。
就其直接作用机制而言,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本质是借壳方股东与上市公司签订合同,内容是就借壳方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明确借壳方股东向上市公司提供利润补偿的方式和数量,故借壳方股东作为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务人。由于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无法对上市公司的原控股股东形成直接限制。从业绩补偿协议的常规约定内容来看,[64]业绩补偿协议并不直接介入原控股股东与其他公众股东之间的关系,无法提供任何针对大股东的约束机制;也无法改变控制权交易作为原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有限次重复博弈中最后一次博弈的属性;同样无法为中小股东提供介入控制权交易或分享溢价的任何可能。由此,业绩补偿协议本身无法直接处理控制权交易中控制权溢价的风险。
对于新股东进入后不善经营导致公司业绩下滑、影响公司和公众股东利益的风险,尽管借壳方股东的业绩补偿承诺提供了直接的兜底保障,但其“兜底性”显然不如传统资产重组交易中的业绩补偿承诺,原因是借壳方股东获得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具体而言,借壳方股东控制上市公司后,不仅能够采取短期主义的公司政策和商业模式来获得快速但潜藏隐忧的业绩上涨和股价拉升,也有能力通过各类合法或违法的法律和会计处理粉饰上市公司的业绩,以满足盈利预测的要求,免去补偿义务。因此,从长期来看,业绩补偿承诺不仅无法直接为新股东经营不善的控制权交易风险提供保障,反而可能会向借壳方股东施加采用短视经营模式乃至违法商业模式的负面激励,放大新股东不善经营的风险。
控制权溢价的现象在中公教育借壳亚夏汽车上市的交易中有所体现,中公教育股东方购买新股的价格(3.27元/股)与收购亚夏实业所持股份的价格(12.69元/股、13.76元/股)存在较大差异,尽管交易公告指出其原因在于两笔交易的定价基础不同,但对于同时发生的“一揽子”借壳上市交易而言,这一解释仍然是形式主义的:将整体借壳上市交易的个别交易步骤单独拆开,每步交易细节欠缺独立的经济合理性,不会单独发生;因此,在同一时点发生、同属一个交易框架中的两笔相同性质交易应统一定价,无论是按照原亚夏汽车的股价标准,或按照中公教育借壳后的预期股价。本文认为,两笔交易的定价基础产生差距的实质原因是,若中公教育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新股,则可获取相对既有公众股东更多的持股比例;而在中公教育股东向原亚夏实业控股股东购买股份的过程中,其高价的性质更像是借壳方股东向原控股股东支付的一笔“贿赂”,同时包括“壳资源”价格与“控制权溢价”,以使亚夏实业放弃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尽管前者在广义上也属于后者的一部分。中公教育的实例说明,业绩补偿承诺实际无法对借壳方向原控股股东支付的控制权溢价形成直接的制约。
就相对间接的作用机制而言,首先,业绩补偿承诺制度似乎能为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和公众股东福利情况提供兜底保障,在上市公司业绩未达协议约定预期时,由新进入的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提供现金或股份补偿,稳定市场情绪和上市公司股价。然而,新进入的控股股东在承诺期内可能因业绩压力而采用短视的经营模式,忽略公司的长期利益,最终造成不利于上市公司及公众股东的结果。例如,中公教育在借壳成功后即采用“高退费协议班”[65]等模式以追求营收和利润,但在承诺期满后即出现了大幅度的业绩跳水现象。虽然目前尚无证据能够证明中公教育签订业绩补偿协议、采取激进的经营策略或盈余管理[66]与其承诺期满业绩跳水之间的因果(causal)关系,但两个现象之间潜在的联系无疑值得警惕,表明业绩补偿承诺可能无法为上市公司的利润提供兜底保障;相反,可能造成财务造假、业绩爆雷与股价崩盘等市场风险,[67]与公司、公众股东的长期利益相悖。
其次,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另一层间接作用机制是,通过协议中业绩承诺与资产估值的挂钩、借壳方股东与原控股股东的利益博弈,间接减弱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获取高控制权溢价的激励。在业绩补偿承诺制度支持者的设想中,尽管借壳方股东可能与原控股股东合谋,原控股股东以对借壳方资产的高估值、借壳方股东能够获取的高控股比例为代价,交换借壳方股东向其支付的高额控制权溢价,但由于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往往对借壳上市类重大资产重组进行实质性审查,对于资产的高估值必然伴随着与高额利润目标挂钩的业绩承诺;由此,借壳方股东可能迫于对高额利润目标的畏惧而放弃对于资产的高估值,其在与原控股股东的谈判博弈中也将尝试降低向原控股股东支付的控制权溢价。循此逻辑,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确能使借壳方资产的估值相对合理,并间接防止控制权溢价过高的风险。但前述逻辑的关键漏洞在于,由于“壳资源”的稀缺属性,原控股股东的谈判力量相较于借壳方股东具有极大优势,借壳方股东谈判以降低控制权溢价的期待容易落空,这意味着控制权溢价很可能不受到业绩补偿承诺的间接制约。更坏的结果则是,借壳方股东尝试降低控制权溢价的数额未果后,产生了“捞一笔”的风险偏好型想法,大方地支付控制权溢价并以此为由要求提高资产估值,在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后再尝试通过激进甚至违法的经营策略和会计处理满足高额的盈利预测,最终加剧了控制权交易的风险。
四、业绩补偿承诺的制度解释:“承诺—免责”模式的延续
从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实际运行的直接、间接机制来看,其无法应对借壳上市中的控制权交易的风险。那么,监管机构为何要在2014年对业绩补偿承诺制度进行目的上的调整?借用一个进化论视角下的隐喻(metaphor), “这个监管技术是一个令人迷惑的物种,在所有环境里都能迅速繁衍,但很少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些不适应环境的监管技术为什么能存活呢?”[68]本部分尝试为其提供一个制度层面的解释。这种分析思路并不试图完全还原历史事件的全貌与其中的微观决策原因,[69]即无意探究监管机构的决策者为何在2014年的具体时点选择将业绩补偿承诺制度针对性用于借壳上市交易,这显然包括很多可能性,如特定时点的集体讨论的结果、研究者与市场主体的建议、重大事件的冲击,等等;其也并非严格的因果识别或推断(causal inference),即并不试图严格测量本文所提出的主张能够为监管失败的现状提供多大的解释力与可信程度。制度层面的分析与解释,更侧重于借鉴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视野下的宏观分析思路,[70]从广义的制度层面(包括狭义的制度、模式、文化、社会规范等)探讨监管机构采取失败或无效策略的原因。这一分析思路在法学领域也已经得到部分学者采纳,[71]其中比较典型的是Ben-Shahar和Schneider对强制信息披露(mandatory disclosure)制度虽无效但持续存在的政治(politics)原因展开的分析。[72]
在功能意义上,业绩补偿承诺制度不仅意味着借壳方股东需要与被借壳方股东、上市公司友好合作,提供业绩补偿承诺以获得监管方对其借壳上市交易的“放行”,[73]更意味着监管方能够通过促使借壳方股东提供业绩补偿承诺而“尽其责”。前者涉及传统规制研究中的监管权力与市场互动,[74]后一层含义则属于官僚组织研究的范畴,即监管者由于受到上级长官、议事机构等权力授出方的监督与压力,负有妥善监管的责任。监管方的目标或责任不仅包括市场运行的经济效率,还包括股民情绪、市场稳定[75]等。[76]借壳上市交易中的监管方通过强制被监管方出具业绩补偿承诺,后者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股票、现金等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为交易完成时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股东福利情况等提供实质保障。尽管按照前文的分析,其无法在经济效率上应对控制权交易的风险,但“兜底”式的安排至少能够稳定股民情绪,保障市场相对稳定。因此,业绩补偿承诺的达成不仅是被监管方完成交易的核心步骤,同时还意味着被监管方对交易结果的保证,更表明监管方已经履行其职责,其维持市场稳定的任务将向被监管方部分转移。
本文认为,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承诺—免责”式的安排。在一般化意义上,该模式的三个要件分别是:(1)被监管方为交易结果提供实质保证的承诺是制度核心;(2)监管方的责任部分向被监管方转移;(3)被监管方以此获准交易,监管方以此部分免除其“看护”责任。在既有的证监会监管规则和市场主体交易安排中,存在类似的先例。
证监会的监管实践中存在大量以“承诺”为核心的规则。在“北大法宝”中设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作为文书格式、“承诺”作为全文内容[77]的要求后进行检索,共有114个符合要求的结果,其中现行有效的结果为45个;设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作为文书格式、“承诺”作为全文内容的要求后进行检索,共有256个符合要求的结果,其中现行有效的结果为135个。尽管多数规则并不与“承诺—免责”模式直接相关,[78]但至少能够反映出证监会将承诺本身作为其事前监管、行政执法、事后监督执行的抓手之一。[79]而部分制度能够体现出“承诺—免责”模式的部分特征,如基金机构高管的选任制度要求提名人就拟任人符合任职条件出具书面承诺,[80]这实际上是要求提名人为拟任职者从事基金管理的能力作出保证,监管方据此将部分监督基金机构管理层选任的责任转移至提名人方。
由证监会推行的最为典型的“承诺—免责”监管模式,体现在2005年至2008年进行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证监会、国资委等牵头部门认为,非流通股股东作出并履行承诺有助于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流通股股东分享改革红利、我国上市公司由股权分置状态向全流通时代平稳过渡的前提。[81]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对其自身施加了让渡经济利益的义务,从而为交易完成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供了兜底保障,证监会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的责任由此部分转移至非流通股股东。非流通股股东作出并履行承诺自然成为整体改革方案的重点之一,一方面作为股权分置方案通过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是监管方尽职和事后免责的要求,“……对相关当事人……兑现改革承诺……实施持续监管”[82],“非流通股股东要严格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83],上交所、深交所也迅速联合出台细则予以跟进。[84]事实上,尽管股权分置改革时期中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内容各异,但其中与业绩挂钩的承诺甚至可以认为是现行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雏形版本,如深交所在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承诺事项管理指引》中明确提及与具体业绩挂钩的承诺类型,[85]也有研究指出,“上市公司大规模的业绩承诺现象始于股权分置改革……证监会和各交易所特别要求股权分置改革与资产重组相结合的上市公司,需要对未来的经营目标作出明确的承诺并予以披露”。[86]
在市场主体的实践中,符合“承诺—免责”监管模式的安排是对赌协议。商事交易与组织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常常需要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机关[87]或当事人之间的合约安排来实现监督和风险控制。后者的体现即对赌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88]以与大股东对赌的现金补偿型安排为例,拟向公司投资的小股东具有监督大股东妥善经营公司的诉求,经由对赌协议,大股东能够为对赌期限届满时的小股东利益提供保证,小股东由此将其作为公司股东的风险、作为治理参与者与投资者的监督责任部分转移给了大股东,因此,对赌协议成为整个投资交易能够达成的关键一环。对赌协议通过被投资公司或其大股东的补偿承诺安排,能够部分转移投资者的监督责任并提供经济利益的保障,在“直接融资发展水平依然偏低,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规模较小、股票融资功能有待改善”[89]的我国公司投融资市场上,得到了强势投资者们的高度青睐和广泛应用。
从制度比较的视角来看,借壳上市中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股改中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制度与投资实践中的对赌交易安排存在高度相似,都能够通过“承诺—免责”的模式进行解释。因此,依托于既有社会科学研究在制度变迁中所提出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90]、制度惯性或黏性(stickiness)[91]等理论,一个大胆的猜想是:在资本市场建设的制度起点,由于问责体制、可用资源、组织特性等的制约,“承诺—免责”模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监管者和市场主体在应对复杂交易时常见的制度设计,并对后续有权机关的监管规则和市场主体自发的商事安排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后者并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体现了“承诺—免责”模式的不断复制、加强和演化。
从前文所归纳的三个要件和具体实践来看,“承诺—免责”模式的监管思路至少具有以下四重描述性的特征:(1)命令控制(command-control)[92]式的,被监管方的承诺往往是强制性或准强制的安排;(2)非常注重交易的形式化结果,要求被监管方承诺为交易提供差强人意的保障,即使此种安排在实质上是不效率的;(3)强调责任的减免和转移,即(准)监管方能够通过这一制度安排部分摆脱潜在的责任、交易风险;(4)以市场稳定作为其核心目标。而其他国家在相似情形下的监管制度(以美国为例)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借壳上市对应的控制权交易风险应对中,美国资本市场不仅选择倚仗常规的董事诚信义务制度,[93]还特别地要求控股股东向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94]以保障小股东的权益不会因控制权过度溢价、掠夺式收购等受损。又如,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安排中,美国市场的基本应对方式是“分期融资机制”(staged finance),其实质是赋予投资者以一个有价值的期权,在每个阶段结束时根据目标公司经营状况选择是否继续投资,使投资者能够“通过分期出资、及时止损的安排来降低初始投资估值过高可能带来的损失”;即使在近年来美国市场也开始出现估值调整观念,但也并非是中国版本的现金补偿,而是调整特定投资者所持有的股权比例,并通过棘轮条款(Ratchet Protection)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95]对比而言,前述美国式监管模式的特点是:(1)更加灵活的相机(discretionary)决策;(2)通过各阶段更准确、细致的调整机制来保证交易的实质公平;[96](3)要求监管方在交易的各个阶段都履行看护的职责,且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
由此观之,我国的交易实践与监管实践中的“承诺—免责”模式与域外资本市场风格迥异,其三个要件、四个制度特征甚至可以被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基因”(Institutional Genes)[97]。当证监会在抉择采取何种模式以应对借壳上市中的控制权交易风险时,降低自身监管责任与风险的刚性需求、“稳定压倒一切”[98]的明线目标、监管手段的自我更新困难[99]、继续采纳“承诺—免责”模式的较低成本,使证监会倾向于复制过往的监管模式。因此,在借壳上市中,证监会生硬地将交易的资产重组属性作为抓手,通过具有“承诺—免责”属性的强制业绩补偿承诺制度介入其中,虽然看似能够保障上市公司权益、维护市场稳定、完成监管职责,但实际上无法应对控制权交易的风险,甚至向借壳方股东施加了错误的激励,最终损害了社会总体福利。
总之,借壳上市中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可以被认为是“承诺—免责”模式在我国资本市场复制与演化时的一个样本。尽管这更接近于一种假说或猜想,缺乏完整的因果机制和实证支持,但起码尚未被证伪,也能从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寻求理论资源、从既有的资本市场实践中找到初步的经验证据,对于目前尚待探索的、超越具体制度层面的资本市场“中国模式”来讲,“……合乎逻辑的猜想自有其学术价值,即使它在未来可能会被部分(甚至全部)证伪”,而本部分想要提供的正是一种留待后续实证研究与理论跟进的理论(idea or theory)方向。[100]当然,我国资本市场“承诺—免责”模式根源的更进一步探究,正如一国的董事会治理模式往往受制于或主动模仿该国的政治制度,[101]也同样应当追溯至我国的官僚制度[102]、严格的问责模式与规避责任的强激励[103]、稳定居于优位的治理目标排序和“有司之事”的履职传统[104]等政治制度之中。
五、结语
我国A股市场借壳上市的本质是控制权交易,监管机构所推行的类似“买方对赌”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具有中国特色,但隐含着制度与风险“关公战秦琼”的错位隐忧。从实证法规则的变迁来看,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出台时的制度目的是用于应对资产重组交易中的资产溢价风险,但在2014年的规则修订中,监管机构针对性地将其用于应对借壳上市中的控制权风险,缺乏审慎的考虑,更可能是制度惯性的安排。业绩补偿承诺制度不仅无法应对借壳上市中的控制权交易风险,甚至会对上市公司的新旧控股股东造成不利于长期公司绩效和股东福利的负面激励,未经审思的监管无法通过社会效率的考验。作为本土制度,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监管者应对借壳上市中控制权交易风险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105]智慧,但其在制度设计上终归有“无心插柳”的偶然,这使其难免落入制度错位、监管失败的窠臼。
“大象在房间里”,对于深深嵌入“配额制”(quota system)[106]、央地关系[107]等政治经济背景的我国证券市场,即使在证监会自2014年以来不断收严借壳上市规则[108]、2020年经由《证券法》修改全面铺开注册制改革的情况下,改革的渐进性质与监管机构不时的“IPO窗口指导活动”[109]使其仍然作为我国公司登陆公开市场的重要选择之一,[110]借壳上市中的控制权交易风险也仍然值得关注。对于未来风险应对方案的选择,究竟是维持现行“买方义务”式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111]还是取消借壳上市的强制要约豁免以消除溢价可能,[112]抑或选择以诚信义务为核心的“卖方义务”方案,[113]亟待监管者进行回应。
法律制度是建设强大资本市场的前提已经成为共识。[114]从制度变迁层面的作用机制来看,业绩补偿承诺制度不过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应对复杂交易时常见“承诺—免责”模式的复制或延续,后者本身的利弊并未得到学界和政策界的认真对待,而其改革的方向恐怕才是我国资本市场真正进入“高质量发展”[115]的关键。决策者应该意识到,在匮乏于理论自觉时,实用主义的智慧与对既有模式的路径依赖之间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注释:
[1] 开创性的研究,See Henry G. Manne, Merger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 conomy, Vol.73, No.2. Apr., 1965, pp.110-120.20世纪80年代有关控制权溢价的代表性研究,See Michael C. Jensen and Richard S. Ruback,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1983), pp.5-50.
[2] 参见肖钢:《中国资本市场变革》,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页。
[3] 参见MBA智库百科:“宝延风波”词条,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10月5日。
[4] 按照公开媒体报道中的相关数据,以“控制权变更”作为判定控制权交易发生的标准,(1)2014年至2018年A股市场上分别发生了89起、85起、62起、85起、136起控制权交易,参见新京报:《A股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降温”》,2019年6月17日电子版,B06版;(2)2019年A股市场上发生了165起控制权交易,参见中国证券报·中证网:《今年以来165家公司控制权变更:国资背景主体接盘案例增加》,https://www.cs.com.cn/ssgs/gsxw/201912/t20191225_6011550.html, 2019年12月25日发布,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10月5日;(3)2020年、2021年A股市场上都发生了220起左右的控制权交易,剔除无偿划转、继承/家族内部安排、被动减持等被动行为导致的控制权变更后,分别发生了101起、106起控制权交易,参见经济观察网:《悄然变化的A股并购生态》,http://www.eeo.com.cn/2022/0628/541162.shtml, 2022年6月28日发布,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10月5日。(4)对于2022年的情况,截至6月2日,A股市场上有66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参见吴晓璐:《年内A股并购项目共2645单数量同比增逾两成》,载《证券日报》,2022年6月3日发布,https://finance, china.com.cn/stock/zqyw/20220603/5819445.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10月5日。
[5] 国内针对收购上市公司的监管规则的反思性、批评性研究,参见薛人伟:《论中国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之合理性——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彭冰:《法国SEB集团收购苏泊尔案分析》,载《商事法论集》2010年第1辑。Bebchuk的研究也认为过于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不利于保护投资者和促进效率, See Lucian A Bebchuk and Robert J Jr Jacks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Block - holder Disclosure, (2012)2 Harvard Business Law Review 39, pp.39-60.
[6] 参见人民日报全媒体:《证监会主席怒批资本市场“野蛮人”称资产管理人不能做“妖精”》,载环球网,2016年12月4日发布,https: //china, huanqiu.com/ajrticle/9CaKmJYZlY,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7月4日。
[7]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1页。
[8] 参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13条的具体规定。
[9] 在该市场上交易的商品被称为“壳资源”,参见朱宝宪、王怡凯:《1998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实践的效应分析》,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
[10] 例如,尽管美国、中国香港等地的证券市场中也存在借壳上市实践,还在近年来创造了类借壳上市的特殊目的公司(SPAC)形式,但并不存在类似我国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监管规则。参见马骁、刘力臻:《中、美及香港证券市场借壳上市监管制度比较》,载《证券市场导报》2013年第3期。
[11] 主要参见甘培忠:《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0页、第177-178页;朱锦清:《公司法学(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211页;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5-672页。
[12] 少量针对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如何影响借壳上市的研究,参见宁清宇:《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业绩补偿制度研究》,载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编:《金融法苑(2015总第九十一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年版;吕晖:《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制度的取消——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载彭冰主编:《金融法苑(2021总第一百零六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22年版。但前述研究重点关注的仍然是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资产重组交易面向,且具体的分析论证并不令人满意。
[13] 在借壳上市交易中,借壳方是拟上市的公司,但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上是借壳方的股东。
[14] 若无特别说明,本文在A股市场的背景下使用“控制权”一词时,其含义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版)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15] 参见陈冬、范蕊、梁上坤:《谁动了上市公司的壳?——地方保护主义与上市公司壳交易》,载《金融研究》2016年第7期。事实上,本文认为,即使在科创板、创业板已经开始实施注册制的当下(21世纪20年代),中国的IPO准入也仍然较为严格。
[16]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13条:“……(1)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100%以上;(2)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100%以上;(3)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100%以上;(4)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100%以上。”
[17] 重大资产重组的定义,请参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之外购买、出售资产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达到规定的比例,导致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交易行为(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18]《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16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中国证监会2020年7月。
[19] 在借壳上市之外的其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出具业绩补偿承诺的一方是出售资产的“卖方”,实际上类似于PE/VC “对赌协议”中的“卖方对赌”,但这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参见刘燕:《“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8页;同时参见“方达律师事务所”公众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业绩对赌》系列文章,2020年11月16日至2021年2月23日发布,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7月4日。
[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2019年11月8日发布,第2条。
[21] 中公教育:《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4月28日发布,第6页。
[22] 交易所发出的关注函中,第一次关注函请参见深交所:《关于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349号);中公教育的回应,请参见中公教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2021年10月30日发布。第二次关注函请参见深交所:《关于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439号);中公教育的回应,请参见中公教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2021年12月29日发布。深交所:《关于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491号),2022年6月8日发布;转引自中公教育:《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2022年6月22日发布。交易所发出的问询函,请参见深交所:《关于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491号),2022年6月8日发布;转引自中公教育:《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2022年6月22日发布。
[23] 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第0232021010号),2021年12月15日发布;转引自中公教育:《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2021年12月17日发布。同时参见中公教育:《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022年4月27日发布。
[24] 参见王宇:《公务员考试火爆公考培训爆雷?》,载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访问地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al HHhcvJZ_wl amWVYIc5HQ,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11月14日。
[25] 由于相关资料烦琐,本文统一将刻画中公教育借壳亚夏汽车上市所涉及的实践资料归纳于此脚注下。参见亚夏汽车:《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2018年12月1日发布;亚夏汽车:《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2018年11月3日发布;亚夏汽车:《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2018年12月1日发布;亚夏汽车:《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的公告》,2018年12月28日发布;亚夏汽车:《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2018年11月发布;亚夏汽车:《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2018年11月发布。
[26] 由于亚夏汽车颁布的分红计划,对于亚夏汽车的资产作价存在调整,但此处为行文简便,不再赘述。
[27] 尽管亚夏汽车在其公告中对这一点的合理性、合规性及利益输送情况进行了特别说明,认为两笔交易的定价基础不同,前者以亚夏汽车的股价为基础,后者则以重组完成后作为上市公司的中公教育预期股价为基础。参见亚夏汽车:《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2018年11月发布,第34页以下。
[28] 实际上还存在发行新股、股份转让等交易类型,但其在整体借壳上市中的辅助性明显,故在此不赘述。
[29] 参见张海晴、文雯、宋建波:《并购业绩补偿承诺与商誉减值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20年第9期,第44-54、77页。
[30] See Simon Johnson, Ral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Tunne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2, 2000, pp.22-27.同时参见赵骏、吕成龙:《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的隧道阻遏研究》,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
[31]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622页。
[32] 对于控制权溢价的分配而言,(1)有利于中小股东的一派观点是Andrews主张的“均等分享派”(equal sharing approach or equal opportunity rale),最早可追溯自Berle处,尽管后者更为极端,认为控股股东享有的权益属于“公司资产”(corporate asset),其要求对所有股东平等地分享控制权收益,要求等比例地向购买者出售股份, See Adolf A. Berle &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m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revised edition 1968, pp.207-252; Adolf A. Berle, “Control” in Corporate Law,58 Columbia Law Review 1212(1958), pp.1212-1225; Adolf A. Berle, The Price of Power: Sale of Corporate Control, 50 Cornell Law Quarterly 579(1964), pp.628-640; William D. Andrews, Stockholder's Right to Equal Opportunity in the Sale of Shares, Harvard Law Review, Vol.78, No.3, January 1965, pp.505-563.(2)与之相对的流派是“市场派”(The Market Rule),以Easterbrook和Fischel为代表,他们的主张是控股股东有权享有控制权收益,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Corporate Control Transactions, 91 Yale Law Journal.698, 1982, pp.698-738.; Sale of Corporate Contro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Summer, 1952, Vol.19, No.4, pp.869-872.(3)居中的流派则以Bebchuk为代表,主张前述观点各有利弊,市场派的观点有利于促进更有效的控制权交易,而均等分享派的观点则有利于防止更差的控制权交易,但Bebchuk则更加偏向于市场规则(Market Rule),因为市场规则总是能增加社会总福利,尽管有时候会降低某一方私人主体的福利, See Lucian Arye Bebchuk, Efficient and Inefficient Sales of Corporate Contro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 1994, Vol.109, No.4, pp.957—993.
[33] 参见[美]罗伯特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李存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以下;[美]罗伯特克校克:《公司法则》,胡平、林长远、徐庆恒、陈亮译,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408页。See also Franklin A. Gevurtz, Corporation Law (second edition), WEST, pp.662—675.
[34] 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262页。
[35] 讨论信息不对称的经典文献,See G.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1970, pp.488—500.; Joseph E. Stiglitz, Equilibrium in Product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2), May 1979, pp.339—345.
[36] 针对借壳上市各方利益博弈的更详细说明,请参见本文第三部分“三、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借壳上市中的监管失败。
[37] 一般认为,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百四十九条确立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义务,但学界几乎没有观点认为《公司法》确立了后文将要谈及的控股股东诚信义务。
[38] See Roscoe Pound, 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 American Law Review, vol.44, no.1, January-February 1910, pp.12-36.
[39] 参见[美]劳伦斯·弗里德曼:《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邱遥堃译,侯猛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页。
[40] See S. J. Li e bo wit z and Stephen E. Margolis, Path Dependence, Lock-in, and Histor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Apr., 1995, Vol.11, No.1, pp.205-226, at p.207 and p.216.
[41] 参见赵立新、姚又文:《对重组盈利预测补偿制度的运行分析及完善建议》,载《证券市场导报》2014年第4期,第4-8、15页。
[42]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08年版)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43] 例如在2008年首次规定业绩补偿承诺制度之前就已经发表的文章,参见张红侠:《并购溢价支付风险补偿模型的初步研究》,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81-83页;王立杰、孙涛:《并购溢价支付风险及业绩补偿模型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03年第12期,第20-23页。
[44] 参见孔宁宁、吴蕾、陈绾墨:《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施风险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以雅百特为例》,载《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69-79页;伍晓雯、柳叶:《我国上市公司重组中业绩补偿制度之完善》,载《中财法律评论》2017年第9期,第72-95页。
[45] 参见方重、程杨、肖媛:《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的现况与监管》,载《清华金融评论》2016年第10期,第73-79页。
[46] See Arnold C. Harberger, Issues of Tax Reform for Latin America ,in Fiscal Policy for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5, cited from Eric A. Posner and E. Glen Weyl,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at p.57.对其交易制度、周转率等因素进行改进的版本是COST (Common Ownership Self-Assessed Tax)系统;See Eric A. Posner and E. Glen Weyl,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30-79.
[47] See Michael. Spence,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7, No.3(Aug., 1973), pp.355-374.; Michael. Spence, Signaling in retrospect and the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of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3), 2002, pp.434-459.
[48] 参见王建伟、钱金晶:《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问题及监管对策研究——基于深市并购重组交易的经验数据》,载《证券市场导报》2018年第10期,第44-51页;张琴:《并购重组业绩承诺与公司绩效》,载《财会通讯》2019年第36期,第64-68页;参见罗喜英、阳倩:《业绩承诺能否为上市公司高溢价并购买单?——基于* ST宇顺并购雅视科技的案例分析》,载《中国注册会计师》2017年第3期,第61-65页。
[49] 参见许艺铧、杨野、王媚莎:《高额业绩承诺:保障机制还是套利工具》,载《商业会计》2021年第22期,第67-72页;李晶晶、郭颖文、魏明海:《事与愿违:并购业绩承诺为何加剧股价暴跌风险?》,载《会计研究》2020年第4期,第37-44页。
[50] 参见黄小勇、王玥、刘娟:《业绩补偿承诺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以掌趣科技收购上游信息为例》,载《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48-57页;窦超、翟进步:《业绩承诺背后的财富转移效应研究》,载《金融研究》2020年第12期,第189-206页。
[51] 参见李井林、戴宛霖、姚晓林:《并购对价与支付方式:业绩承诺与风险承担——基于蓝色光标并购博杰广告的案例分析》,载《会计之友》2019年第20期,第61-66页;吕长江、韩慧博:《业绩补偿承诺、协同效应与并购收益分配》,载《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第3-13页;尹美群、吴博:《业绩补偿承诺对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效应——来自中小板与创业板的经验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第53-67页;郑忱阳、刘超、江萍、刘园:《自愿还是强制对赌?——基于证监会第109号令的准自然实验》,载《国际金融研究》2019年第5期,第87-96页。
[52]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版)第三十五条第三款:“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资产且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的,不适用本条前二款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可以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是否采取业绩补偿和每股收益填补措施及相关具体安排。”2020年颁布的现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延续了这一规定。
[53] 在讨论中,任孝民博士指出,监管机构在涉及控制权转移的资产重组交易中强制推行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原因还可能在于:(1)“大股东”的承诺是中国证券市场常用的类监管手段;(2)业绩补偿承诺在借壳上市中起到了类IPO资质审查的效果。由于监管方并未对规则起草的原因进行正式解释,本文同意这一主张的可能性,但从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实证法规则变迁过程来看,本文的观点是更为妥当的。
[54] “本次交易完成后,李永新和鲁忠芳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参见亚夏汽车:《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2018年11月发布,第115页。本文未在该文件所引用的具体监管规则中找到将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的直接规定,可能的原因是监管机构在这类交易中对关联关系进行了实质认定。
[55] 可资类比的是非重大资产重组情形下的控制权交易,设若A公司的控股股东某甲拟将该公司出售给素昧平生的某乙,则按照“潜在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的关联关系认定标准,这一交易似乎也属于关联交易。因此应认为,“潜在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的关联属性实际上来源于控制权交易。
[56] 本文对于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实证法层面的考察,以这一制度的定位在实质上发生改变为主要讨论对象,因此仅仅选择了2008年、2014年、2020年(现行有效)版本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进行分析,不涉及其他更低层级的规则。
[57] 若考虑到借壳上市同时构成资产重组交易,则作为主体的上市公司亚夏汽车实际上向中公教育股东方购买了中公教育的全部股份这一资产,上市公司亚夏汽车(而非亚夏实业)和中公教育作为资产买卖双方对于资产的对价、后续盈利情况等相关的博弈关系也属于一组利益冲突。但本文的重点并非讨论借壳上市中的资产重组交易属性,故不在正文中加以赘述。
[58]委托代理关系的相关讨论;See Reinier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9-32.
[59]有关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的一般性说明,See Steven Tadelis, Gam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90-219.同时参见[美]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九版),费方域、朱保华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375-376页。
[60] 中公教育:《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4月28日发布,第33页。
[61] 亚夏汽车:《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2018年11月发布,第112页。
[62] See Reinier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9—32.
[63] 根据亚夏汽车披露的信息,借壳上市交易前亚夏汽车其他股东持股56.29%,但在借壳上市交易完成后其持股比例下降到&38%,参见亚夏汽车:《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2018年11月发布,第111页。
[64] 参见亚夏汽车:《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第635-639页。
[65] 参见财新网:《特稿|公考龙头业绩“跳水”溯源》,2021年10月31日发布,https://www.caixin.com/2021-10-31/101793999.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7月7日。
[66] 参见张海晴、文雯、宋健波:《借壳上市中的业绩补偿承诺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陈远志、张元新:《并购业绩承诺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中介效应的检验》,载《财会通讯》2021年第10期。
[67] 参见每日经济新闻:《三年业绩承诺期过后就变脸上市公司高估值并购商誉变“伤誉”》,2018年9月18日发布,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9-18/1256285.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7月7日。相关研究,请参见王竞达、范庆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业绩承诺及政策影响研究》,载《会计研究》2017年第10期,第71-77、97页;张冀:《深市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及商誉情况分析》,载《证券市场导报》2017年第11期,第28-32、40页;关静怡、刘娥平:《业绩承诺增长率、并购溢价与股价崩盘风险》,载《证券市场导报》2019年第2期,第35-44页。
[68] Omri Ben-Shahar and Caxl E. Schneider, More than You Wanted to Know: the Failure of Mandated Disclos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at p.138.
[69] 借用赵鼎新教授的话来说,本文并不试图探究“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特殊性机制”,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普遍性机制”。参见袁春希:《中国的儒法传统,为何如此根深蒂固?专访赵鼎新》,载“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2022年8月14日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YhyxFufghcJJDzaiVUNqKg,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11月30日。
[70] 当然,其他学科中也有类似的主张,如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See James 0.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 78(September):734-749.; Michael G. Roskin et al.,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fourteen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6, at pp.15-22.具体问题上的应用,See also Xue, Melanie Meng, Autocratic Rule and Social Capitals Evidence from Imperial China, November 7, 202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85680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m.2856803.社会学中“制度学派”的相关研究,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64-110页;[英]玛丽·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张晨曲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See also Zhou Xueguang,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COVID -19 Crisis: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nd Its Resilien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6:3, July 2020, pp.473-484.
[71] See Angela Huyue Zhang, Agility Over Stability: Chinas Great Reversal in Regulating the Platform Economy,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63(2), 2022.; Deng Jinting & Liu Pinxin, Considtatwe Authoritarianism: The Drafting of Chinas Internet Security Law and E-Commerce Law,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107, 679-695.
[72] See Omri Ben-Shahar and Carl E. Schneider, More than You Wanted to Know: the Failure of Mandated Disclos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at pp.138-151. Ben-Shahar和Schneider指出,其强制信息披露虽无效但持续存在的原因包括:(1)“灾难性叙事”(trouble story)的放大效应,政治系统总是对于真实或想象的灾难非常敏感,媒体、游说组织也会加剧这一效果;(2)政府国库(fisc)成本方面的考虑;(3)制度可能性的丰富;(4)制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相融;(5)“棘轮”(Ratchet)效应;(6)监管者的集体行动问题。
[73] 根据证监会于2016年2月25日发布的工作文件《(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行为(构成借壳上市的)审批》,交易各方向证监会报送的材料中应包括“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的补偿协议”。
[74] 实证性规制研究的代表,See George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2, No.1, Spring, 1971.
[75] 参见新华社:《统筹稳增长防风险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访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2022年5月10日发布,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11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5/10/content_5689503.htm。
[76] See Bmnnermeier, Markus Konrad and Sockin, Michael and Xiong, Wei, China's Model of Manag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2)89, pp.3115-3153.
[77] 在“北大法宝”中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针对业绩补偿承诺制度使用的“补偿协议”作为检索关键词,并设定发文主体为证监会,一共仅22个结果,且几乎都与业绩补偿承诺制度有关,不能反映证监会使用“承诺一免责”模式的广泛性。因此,本文最终选择以“承诺”作为检索的关键词。
[78] 既有规则中与“承诺”相关的表述至少包括:各市场股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中要求控股股东提供的股票限售、股票锁定、减持意向、认购股份、利润分配等承诺;对于“保底保收益”等不当承诺的禁止性规定;等等。
[79] 参见《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16号,主要侧重承诺制度在事前日常监管中的运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94号,主要侧重承诺制度在事后监督执行中的运用。同时参见高振翔:《比较法视野下证券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关键问题研究》,载《经贸法律评论》2022年第2期;陈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反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分析——以虚假陈述型违反承诺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8期。
[80] 参见《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95号,第10条。
[81] 非流通股股东往往对最低持股比例、限售期、转让股份价格、增持股份、追送其他股东股份、制定分红提案、资产重组等事项作出承诺,参见李晓红、蔡奕:《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履行监管与股东权益保护》,载《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4期,第12-14页。
[82]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发〔2005〕86号),2005年9月4日发布,第4条。
[83] 证监会、国资委等:《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5〕80号),2005年8月23日发布,第12条。
[84] 上交所、深交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上证法字〔2005〕7号), 2005年9月6日发布。
[85] 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承诺事项管理指引》(深证上〔2005〕95号),2005年11月9 H发布,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
[86] 参见刘浩、杨尔稼、麻樟城:《业绩承诺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以股权分置改革中的管制为例》,载《财经研究》2011年第10期,第58页。
[87] See Melvin A. Eisenberg, Legal Models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in the Modem Corporation: Officers, Directors, and Accountant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63, no.2, March 1975, pp.375-439.; Melvin A. Eisenberg,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nternal Control, Cardozo Law Review, Vol.19, 1997, pp.237-264.
[88]《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2条。
[89] 易纲:《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载《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第5页。
[90] 参见道格校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9月版,第61页、第121-139页。 See also James Mahoney, Analyzing Path Dependence: Lesson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ndreas Wimmer and Reinhart Kossler, eds., Understanding Change: Models, Methodologies, and Metapho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129—139.
[91] 参见[美]保罗·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
[92] See Robert Baldwin, 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Theory, Strateg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06-111.
[93]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476、681-682页。 See also James D. Cox and Thomas Lee Hazen, Treatise 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Dec.2021 updated., 10.4“The directors'obligation to be attentive”, 10.5“Directors' actions should be the product of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and consideration” and 10.11“The scope of th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duty of loyalty”.
[94]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65页以下。其他概括性的研究,See James D. Cox and Thomas Lee Hazen, Treatise 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Dec.2021 updated., 12.1“The sale of corporate control”; Stephen M. Bainbridge, Corporate Law (third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pp.185-207.; Franklin A. Gevurtz, Corporation Law Second edition), WEST, pp.662-675.这里实际上还存在诚信义务指向的对象是中小股东或公司本身的分歧,本文赞成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对象指向中小股东的观点,See Victor. Bmdney, Fiduciary Ideology in Transactions Affecting Corporate Control, Michigan Law Review, Vol.65, No.2, December 1966, pp.259-300.
[95] 参见刘燕:《对赌协议与公司法资本管制:美国实践及其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143-144页。
[96] 尽管学者的批评表明,特校华州法院新近判例中的审查标准也逐渐沦为形式化,See William W. Bratton, Fair Value as Process: A Retrospective Recons ideration of Delaware Appraisal, October 18, 2022, U of Penn, Inst for Law & Econ Research Paper No.22-38, University of Miami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Forthcoming, available at SSRN: https: //ssrn.com/abstract=4251712.
[97] 这个概念借用自许成钢教授撰写中的著作,Institutional Genes: Confucianism vs. Christianity with Professor Chenggang Xu, SCCEI seminar,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 v=jkAT7GLusS8.同时参见许成钢:《产权与制度基因》,载“大势看财经”微信公众号,2021年12月22日发布。
[98]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79页。
[99] See Robert Baldwin, 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Theory, Strateg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4-135.
[100] 张泰苏:《从“唐宋变革”到“大分流”:一种假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83页。
[101] See Franklin A. Gevurtz,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 Hofstra Law Review, Vol.33, 2004, pp.89-173, at pp.91-92.129-166.同时参见邓峰:《董事会制度的起源、演进与中国的学习》,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邓峰:《中国法上董事会的角色、职能及思想渊源:实证法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
[102] 参见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59-269页。
[103] 参见邓峰:《领导责任的法律分析——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04] 参见[美]詹姆斯·威尔逊:《美国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张海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236页。
[105] 对实用主义的初步介绍,请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7-584页。
[106] See Katharina Pistor and Chenggang Xu, Governing Stock Marke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Lessons from China,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Vol.7, No.1, pp.184-210.
[107] 参见彭冰:《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上市公司治理》,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08] 参见陈选娟、安郁强、林宏妹:《借壳预期与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载《经济管理》2019年第12期,第149-150页。
[109] 参见财新周刊:(IPO为何收紧》, 2020年12月7日出版,https://weekly.caixin.com/2020-12-05/101635961.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7月7日。
[110] 参见贪天一:《战略新兴板搁浅注册制延迟借壳游戏仍将继续》,载《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16年第8期;肖作平、张欣哲:《壳市场复苏并非改革后退》,载《董事会》2021年第4期。
[111] 部分研究认为,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对于借壳上市企业的绩效和风险承担水平等具有正面效应,参见赵立新、姚又文:《对重组盈利预测补偿制度的运行分析及完善建议》,载《证券市场导报》2014年第4期,第4-8、15页;潘爱玲、吴倩、徐悦淼:《业绩补偿承诺影响借壳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吗?》,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部分研究甚至主张,应当将业绩补偿承诺机制延伸适用于IPO审核,参见吴延坤、唐勇:《业绩承诺机制在IPO审核中的应用分析》,载《中国证券期货》2011年第12期,第116-119页。
[112] 这一观点来自彭冰教授评议本文时提出的一种可能。本文初步认为,借壳上市豁免于强制要约制度的正当性来自上市公司的股东会批准,其意义在于保证交易效率,因此对其取消应当慎重。同时,强制要约制度本身对于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意义也正在受到挑战,参见蔡伟:《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再审视——效率视角下的实证分析》,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薛人伟:《论中国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之合理性——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
[113] 这主要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常见方案。我国针对借壳上市的两部监管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仅仅比较粗糙地规定了卖方董事会的义务,如《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更是完全没有确立卖方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表述。即使在我国更广范围的公司法实践中,诚信义务在多大限度上得到确立也是值得质疑的,参见邓峰:《中国公司理论的演变和制度变革方向》,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2期。
[114] See Bernard S. Black,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for Strong Securities Markets, 48 UCLA Law Review 781(2001), pp.781-786.
[115]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https://china, huanqiu.com/axticle/4AC§prsUKU,最后访问时间为2022年11月15日。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沙龙分享群。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点击下方链接保存课件。
点击下载金融科技大讲堂课件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为作者授权未央网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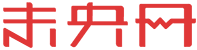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