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分享
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文/郑舒倩,北京大学法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关于证券发行特定对象界定标准的选择,传统分析路径下的各个标准都有其局限性。究其原因在于,难以用某一客观标准来描述“具有自我保护能力”这一抽象、主观的要求。破局之道在于转变制度目的和法律方案的设计思路,承认仅凭特定对象标准的设置无法兼顾投资者保护和融资便利,让非公开发行发挥其便利融资的作用,并通过其他途径增强投资者保护。具体方案包括在司法救济中给予投资者程序法上的优待,以及扩大特定对象范围并引入中介机构对特定对象进行分类。
关键词: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 财富标准 金融经验
我国《证券法》第九条虽然特别规定了“针对特定对象的公开发行”,但与各国界定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的传统思路一致,我国界定公开发行的首要因素依旧是发行对象是否特定。制度设计上,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重要意义在于针对二者的监管逻辑不同,前者强调行政监管,后者侧重契约自治和自律监管。[1]
然而,我国《证券法》未就何为特定对象进行明确,有关股票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的规定中,所谓特定对象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此,可能出现同一群投资者可以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发行,但却不能参与债券非公开发行,出现投资者保护逻辑不一致的情况。此外,从打击金融违法犯罪层面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因发行对象是否特定存疑而难以判断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的问题。[2]可见,统一并明确证券发行环节特定对象标准的内在逻辑,既是保护投资者的需要,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
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经验看,特定对象标准不外乎摘取以下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进行构造:(1)发行对象人数(本文将此类标准称为人数标准);(2)发行对象是否与发行人有特殊关系从而具有信息优势(本文将此类标准称为特殊关系标准);(3)发行对象的富裕程度(本文将此类标准称为财富标准);(4)发行人是否具有投资经验和/或金融相关知识(本文将此类标准称为金融经验标准)。比如,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发行以人数来确定特定对象;[3]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中,投资者可以凭借特殊关系、富裕程度或富裕程度+金融经验成为特定对象;[4]公司债券发行中,特定对象需符合特殊关系标准或财富标准+金融经验标准。[5]此外,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领域也有类似制度设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以特殊关系标准和财富标准来识别合格投资者。[6]
关于特定对象标准的选择,传统上主要讨论如何更为客观、准确地识别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目前较为成熟的投资者适当性分类标准是美国的“获许投资者”定义,该定义以财富标准为核心,我国理论界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或多或少都会提及。然而,从美国SEC最新一次修改“获许投资者”定义的过程看,无法准确描述“获许投资者”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美国实务界和理论界。
那么,为什么有关特定对象确定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各种标准都有何优点和缺憾?在中国法下,如何确定特定对象更合理、更可行?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本文首先遵循传统理论分析路径对各标准的优劣势进行分析,发现现有讨论无法走出困境的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法律解决方案。
一、关于各特定对象标准缺陷的讨论
在存在多个标准的情况下,有必要讨论现有标准是否能够实现制度目的,以及何种标准更有助于实现制度目的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各标准的利弊分析大多基于以下两个方面期待:第一,由于各国私募制度的监管重点在于确保参与私募发行的投资者有能力并且有可能进行自我保护,相应地,特定对象标准应服务于筛选出具备识别、判断和承担风险能力的投资者这一宗旨。第二,从经济效益角度,明确特定对象的外延除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监管成本,还可以减少发行人之间对投资者的竞争,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因此,经特定对象标准筛选后的投资者应能满足市场的融资需求,并且尽可能少地增加融资成本。
在此说明,本文在就各类标准进行讨论时主要以美国获许投资者定义为例。除了我国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大多涉及美国立法及实践外,选取美国为例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首先,我国的私募立法开始较晚,除了2021年公司债券发行方面的特定对象标准有所调整外,[7]立法对该问题没有过多处理,难以比较标准的变化对实践的影响,而美国的相关资料较为丰富。从立法史上看,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我国一样也未明确界定非公开发行,且一开始SEC也比较单一地采用人数标准,随着实践需求的增强,最后确立了非公开发行对象的判断标准,这一点与我国立法的趋势类似。其次,被各国普遍采用且在该问题上争议最大的财富标准起源于美国,由于该标准存在理论缺陷,其存废以及包括我国现行法中以金融经验和最低认购额等修正财富标准等方案在美国均得到较为充分的讨论。再次,美国采用的标准类型最为丰富,其立法史上出现过中国现行法中的人数标准和特殊关系标准。最后,我国的“合格投资者”定义很大程度上借鉴参考了美国2020年修正前的“获许投资者”定义。关于设定特定对象标准的目的,美国SEC的立法资料显示,对获许投资者进行定义旨在“包含那些因其金融经验以及承受损失的能力,或者自我保护能力而不需证券法的注册程序所保护的投资者”。[8]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官方释义明确,“具备相应的识别、判断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是衡量非公开募集基金的投资者是否属于合格的根本标准”,[9]二者相似,因此,在广义证券定义的语境下,我国《证券法》在选择特定对象标准时有借鉴基础。
(一)人数标准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法》在区分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时就采取了人数标准,同时,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时的特定对象也依人数划定,此外,人数多少也是判断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的重要因素。法律对公开发行进行严格监管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投资者缺乏投资知识且难以承受损失风险,但发行人数众多只能代表发行行为具有广泛性,与发行对象是否具有自我保护能力无关。
美国SEC早期也比较强调以人数标准界定公开发行。但是,在1953年SEC诉Ralston Purina一案中,人数标准受到了挑战。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公开”(public)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没有对应一个固定的数值,它的边界数值可以是二,也可以是其他任意值。可能存在一个阈值,使得发行人数超过这个数值时不太可能是非公开发行。SEC当然可以就此确定一个固定的数值,以作为其审查特定豁免申请的阈值,但这种标准是执法标准,不应该成为法律上界定“公开”的定性标准。
除了人数标准,该案中下级法院还提到了以是否公开劝诱和发行范围作为判断标准,即在单位内部发行且不涉及公开劝诱的发行行为不属于公开发行。然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以某个特征来划定一个特定人群没有意义,因为划分标准与划分目的没有关联,所以在界定“公开”时首先应考虑立法目的,进而再选择界定方法。因此,在界定“非公开发行”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证券法为什么要对非公开发行进行豁免。立法资料显示,要求证券发行进行注册是为了确保发行人向投资者充分并公平地披露与发行相关的信息,以便投资者能够作出投资决策。而参与非公开发行的投资者不需要立法的保护。证券法的特别保护是有成本的,既然这些投资者不需要立法保护,那么此种成本是非必要的。因此,非公开发行主要面向能够自我保护(fend for themselves)的投资者。也就是说,豁免条件是:(1)发行对象是具有风险识别能力的成熟投资者(sophisticated investor);(2)发行对象是基于某种关系,能够获取那些本来需靠注册才能获取信息的投资者(特殊关系标准)。[10]
该案中,人数标准因对于实现立法目的没有裨益而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定。该案后,人数标准虽然没有被彻底取消,但也因此没落。通常,SEC根据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来界定非公开发行。关于发行对象,则采用Ralston案确立的成熟投资者和特殊关系标准来认定。
(二)特殊关系标准存在的问题
如联邦最高法院在Ralston案中提到的,非公开发行豁免旨在纳入能够获取有关公司及非公开发行必要信息的投资者,对于此类投资者,其能够获得至少与公开发行相当的投资信息,从而进行知情投资(informed investment)。特殊关系已为投资者提供必要保护,不需要证券法的注册程序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该标准逻辑上能够自洽,主要问题在于,需要在具体情境中对特定投资者的资格进行认定,发行人在发行前需要付出较高的确认成本。并且,由于不够客观、无法标准化,发行人无法确定其发行属于非公开发行并享有豁免,其面临发行行为被认为构成非法集资的风险,因而不受发行人欢迎。[11]经典案例“吴英非法集资案”便体现了该标准的模糊性[12]:吴英的直接集资对象中包括部分资金掮客,这些资金掮客与吴英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看起来符合特殊关系标准,但这一抗辩并未被认可,理由在于,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以人际关系为纽带进行集资是民间融资活动的一大基本特征,若据此认可该抗辩,会有大量类似的民间融资被合法化,进而对金融秩序造成重大冲击。[13]
(三)财富标准的兴起及相关争议
Ralston案中提出的“成熟投资者”虽然相较于人数标准更为合理,但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为解决该问题,SEC于1974年发布规则146,要求拟进行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只能向其有合理理由相信具有投资所需的必要知识和经验,或者有经济上的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发行证券。并且,要求发行人确保受要约人在发行过程中及证券销售前有途径获取信息或已被提供信息。然而,规则146所细化的标准依旧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并不能有效解决实践操作难的问题。[14]
1980年,规则242替换了规则146,该规则采取客观标准来降低发行豁免的不确定性,并将“获许投资者”概念引入美国《证券法》。该规则下,“获许者”(accredited person)被定义为购买10万美元以上(含)所发行证券的个人,发行人的董事或执行官,或特定类型的实体。1982年,《条例D》颁布,同时,规则242被撤销。《条例D》的规则506允许发行人向不超过35名非获许投资者(non-accredited investors)以及不受数量限制的获许投资者进行非公开发行。规则501采取了财富标准和特殊关系标准来界定获许投资者,该规则下的标准较此前的规则242更为详尽。[15]
财富标准就此诞生,它是SEC尝试描述“成熟投资者”的产物。从1974年发布的规则146到1980年的规则242,再到1982年的《条例D》,发行对象的界定标准经历了从主观到客观且确定性逐渐提高的变化,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管和市场对特定对象标准的期待。
无论对于发行人、投资者还是监管者而言,财富标准都更容易适用。《条例D》,尤其是规则506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市场结构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6]推动了美国私募的蓬勃发展,自此,众多国家都走向了以财富标准来确定非公开发行对象的道路。[17]然而,因理论上存在缺陷,该标准引发了很多争议。
财富标准的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拥有财富并不意味着具有风险识别能力从而无需证券法提供保护。[18]二是财富标准阻止了普通投资者通过合理投资积累财富,令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详言之:
首先,财富标准可能纳入了那些不具有足够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富裕并不代表投资者的成熟度,更不等同于自我保护能力。[19]投资能力是多维的,包括但不限于分析风险和回报的能力、评估/减轻/规避风险或损失的能力、合理进行投资分配的能力、获取发行人或与投资相关信息的能力、承担损失的能力。财富的积累不依赖投资(比如继承),拥有巨额财富的投资者可能不具备任何投资经验和金融知识,也就是说,财富多少充其量只能直观反映投资者承担损失的能力。因此,根据财富标准认定的投资者不一定同时具有金融经验并具有承受损失的能力。美国的安然事件和麦道夫事件都暴露了该问题。麦道夫事件爆发后,人们发现,这个庞氏骗局之所以能持续二十余年,那些最多只对项目进行了简单的形式审查就进行大额投资的获许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s)功不可没。[20]
更重要的是,符合财富标准也不当然意味着投资者具有承受损失的能力。在投资金额或者比例不受限的情况下,即便拥有巨额财富,一旦投资额超过了所拥有的财富,投资者仍然无法承担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投资者的盲目投资行为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21]
其次,财富标准限制投资者的投资机会,可能排除了那些可以依据其净资产、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合理的资产配置结构来进行自我保护的投资者。有研究显示,在公司成长到与同类的公众公司相当的规模前,公司倾向于通过非公开方式进行融资,[22]这期间往往是公司的高速增长阶段。如此,不具备投资资格的投资者无法参与这一高收益阶段的投资。除特殊关系标准所纳入的投资者外,还有部分投资者虽然不够富裕,但其或因学历或工作经验等其他原因对特定市场具有较深了解,具备分析风险和回报、减轻/规避风险或损失、合理进行投资分配,或获取发行人或与投资相关信息的能力。相较于空有财富却没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而言,这类投资者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允许不具有金融经验但具备损失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参与交易,但将具有金融经验但不具备损失承担能力的投资者拒之门外,缺乏合理性。此外,个人投资者过少,使得多数投资机会被机构投资者获得,若机构投资者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潜在的投资者所能供应的融资机会减少,在公司对资本的需求稳定的情况下,资本成本将相应增加。
支持财富标准的观点认为,尽管该标准在理论上存在缺陷,适用该标准可能出现在成熟度上,符合标准的投资者不如不符合标准的投资者,但是,在限制投资者承担风险方面的妥协可以促进有效的资本形成(formation)。[23]从美国的实践看,简明易操作的财富标准在识别不需要证券法的注册程序提供保护的投资者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4]
最后,就财富标准本身而言,衡量财富多少的具体指标主要是总收入和净资产两种,但这两种指标其实也不能有效反映特定投资者的风险负担能力。其一,存在收入的同时存在支出,总收入高并不意味着可自由支配的收入高。其二,净资产指标只考虑总资产与总负债之间的差额,但资产有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之分,若投资者使用流动资产进行投资且未能获得预期回报,投资者可能需要对非流动资产进行折价转化,此时,投资者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25]
此外,财富标准还面临对经济发展适应性低的问题。一方面,通货膨胀将使更多的投资者满足财富标准,其设定的阈值对投资者的保护将随之减弱。[26]另一方面,通货减缩会减少参与私募市场的投资者,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减弱,发行人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满足融资需求,这对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有较多资金需求的公司而言,更为不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会便对获许投资者标准的合理性和适应性问题作出回应,于《多德—弗兰克法案》413(b)(2)(A)要求SEC每四年审查一次与自然人有关的获许投资者条款,以确定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和修改。
(四)关于财富标准的替代性方案
从美国实践看,财富标准是唯一可被广泛适用的标准,[27]三个标准中,只有其最客观且易于操作,其地位至今不可动摇。但是,财富标准的缺陷也很明显:其一是按照该标准并不能准确筛选出无需证券法注册程序保护的投资者;其二是该标准不能及时应对社会变化;其三是该标准本身的指标不尽合理。
1.关于废除或补充财富标准的方案。对于财富标准的诸多问题,有比较激进的学者主张废除财富标准——财富标准是次好的方案,那么倘若能有一个理论上没有缺陷,同时又足够客观从而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那么便可以用之替代财富标准。此类学者通常强调金融知识的重要性,[28]并建议对投资者进行分类。关于分类标准,有不同观点,比如,有建议考虑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获取信息的能力,[29]也有建议基于有关投资者对金融和商业活动的敏感度、特定投资行为等方面的综合考察进行分类。[30]这一方案会带来监管成本的增加,此外,还存在具有金融知识是否就意味着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问题——极端假设,若以是否通过相关考试为标准,对于一个金融系大学生而言,通过考试并不困难,但在其无固定工资收入的情况下,显然不具有风险承受能力。如此,不考虑投资者财富状况仅考察其金融知识看起来同样不合理。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调整监管制度,要求所有投资者都通过已注册的交易商和经纪商,或者投资顾问进行交易。[31]这种方案发挥了已注册机构的看门人作用,但相应地,会出现过多的私人监管者。此外,该方案还会增加这些已注册机构的合规成本。这一方案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这些看门人有多大的权限,其按照什么标准对投资者进行管理,其对于投资者的委托需履行多大程度的注意义务,是否需要对这些投资者进行额外保护等。
2.关于改进财富标准及其具体指标的方案。相较于废除财富标准,更多学者认可财富标准的作用并主张辅之以其他标准或手段。就财富标准纳入了实际上不具有必要风险负担能力的投资者这一问题来看,设定投资限额可作为解决方案之一。[32]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对投资者的潜在风险设置监管限制的同时,也限制了投资者的潜在收益。就识别遗漏问题来看,可以通过增加其他标准来解决。美国SEC在关于获许投资者定义的最新修订中增加获许投资者类别的做法即是这一方案的体现。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可分别面向符合标准的投资者和不符合标准的投资者开放资格考试,以更准确地评估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33]这种二次筛选最大的问题是成本问题和管理问题。
对于财富标准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问题,比较受关注的替代性方案有以下几种:(1)定期对财富标准进行审查;(2)将具体数额改为比例;(3)建立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相关的计算公式。美国采取的应对方式是方案一,此方案的优势在于可更灵活且准确应对社会变化。当然,灵活性伴随着不稳定性,且周期性审查将产生立法成本。方案二能保证法律的稳定性,但有研究表明,比例法会减少获许投资者的数量,并可能增加验证获许投资者资格及其参与发售资格相关的成本。[34]方案三既能节省周期性审查带来的成本,又不需要频繁修改法律,但存在难以确定合理的计算方式这一技术性问题。
就财富标准指标的合理性问题来看,美国SEC曾考虑以最低认购额代替目前适用的总收入和净资产指标。此外,另有观点提出以可支配收入作为指标。[35]二者具有共同的合理性来源,即新指标更能反映投资人的真实财务状况。但由于杠杆的普遍存在,最低认购额在反映风险承受能力方面也有缺陷。可支配收入指标则有认定困难的问题。
从美国获许投资者定义的最新修订看,美国立法上的倾向是扩大获许投资者定义,所采取的方案是保留财富标准并通过列举方式增加其他分类,同时通过四年一次的审查来避免标准滞后于社会发展。具体而言:(1)增加新类别,允许持有专业证书、具有专业职称或持有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认可机构签发的其他证书的自然人成为获许投资者;(2)就私募基金而言,《投资公司法》下发行人的“知识型雇员”(knowledgeable employees)为获许投资者;(3)明确拥有500万美元资产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是获许投资者,将SEC和州注册的投资顾问、豁免报告义务的顾问,以及农村商业投资公司(RBIC)添加到可能符合资格的实体名单中;(4)任何根据外国法设立、拥有超过500万美元符合《投资公司法》2a51-1(b)下“投资”,且非为投资所发行证券的特定目的而成立的实体为获许投资者);(5)所管理资产超过500万美元“家族办公室”及其“家族客户”为获许投资者;(6)在定义中增加“配偶等效”(Spousal Equivalent),以便配偶双方可以集中其资金以达到获许投资者要求。
这一做法反映了便利私募发行的立法倾向。虽然SEC称其希望通过界定获许投资者定义识别的是金融经验和承受损失能力兼备的投资者,但如前所述,仅凭借财富标准,可能纳入那些因缺乏投资经验而无法保护自己的投资者,而从SEC将证书和雇员资格这两个反映投资者成熟度的客观标准作为独立标准看,立法上关注投资者成熟度的目的更多地在于扩大获许投资者范围,而非保护此类投资者,或者说,这种做法暗含着金融经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从我国当前合格投资者定义中将“金融资产”单独作为财富标准的一项指标看,我国立法上似乎也是如此。[36]
(五)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1)以人数界定特定对象有违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初衷。(2)特殊关系标准理论上可以实现制度目的,但具有模糊性,且并非经济的方案,实践中不具有普遍适用性。(3)财富标准与制度目的有出入,其改进方案也不甚完美,但其有实践意义。(4)目前无法寻得一个能够同时准确描述金融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客观标准。
二、关于制度目的和法律方案设计思路的反思
分析至此,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一方面,非公开发行实践要求一个客观的、具体可操作的判断规则。另一方面,自我保护能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基于多方面考量得出的主观判断,很难仅用金融经验和/或财富来表达,更无法对其进行标准化,因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普遍适用,又能完美实现制度目的的标准。换言之,现有的制度目标所设定的要求无法通过设置某个标准直接达到,也正是因此,相关讨论总是能找到某一标准的可攻讦之处。
在此,重新审视制度目的。非公开发行的监管逻辑是希望通过发行对象定义识别能够自我保护的投资者,但是,这些投资者是否真的能够进行自我保护?
相较于非公开发行,公开发行提供的投资者保护主要体现在:(1)保障招股说明书等注册文件所反映的投资标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2)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减少“社会和工业顽疾”。为达到类似的效果,非公开发行的参与者需要有渠道获取充分的信息,并有能力在众多信息中筛选真实有效的信息。理论上,特殊标准下的投资者具备该能力。但在此之外,在发行人不主动提供信息的情况下,那些老练的投资者即便具有敏感的信息识别能力,其同样受制于信息不充分问题,而那些空有财富基础但投资经验不足的投资者面临的境况只会更糟。
关于限制对非公开发行进行监管的另一重要理由是,私人定制(private ordering)的投资合同,以及诸如尽职调查、声誉等非正式手段(informal means)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投资风险。[37]然而,通常只有大型投资者具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来定制投资合同或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并且,若大型投资者可以通过谈判获得个人利益,其对发行人所提供格式条款质量的敏感性将降低,对条款质量影响最大的边际投资者(marginal investor)反而缺乏议价能力。[38]也就是说,非公开发行的参与者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具有自我保护能力。换言之,即便我们寻得了一个能够准确描述成熟投资者的标准,经由该标准筛选出来的投资者也并不总是具有自我保护能力。[39]
如此看来,在监管投资者而非发行人的逻辑下,不论如何调整特定对象的定义,其对投资者的保护始终有疏漏。通过界定特定对象来区分投资者是否需要保护的意义不如想象中那般重大。
如果转变制度目的和评价标准,前文所述的诸多问题可能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总的来说,各种发行制度都是在便利融资和保护投资者之间寻求平衡。从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看,在工业化国家,私募发行、私募市场一般都是先于公开发行、公开市场出现。以美国为例,1800年费城出现美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之前,从事制造业的公司都是通过由商人阶层认购即私募来完成融资。其后30年里,美国工业也仍然主要依赖自身积累再投资,以及与企业相关的人直接投资取得发展。直到19世纪30年代铁路开发热潮兴起带来资金需求的激增,吸引公众投资的行为才大量出现。在此期间,农夫、小商人等不成熟投资者与高风险证券的错配,以及日渐严重的欺诈问题造成市场混乱,一些州发布了铁路建设证券相关规定。20世纪伊始至大萧条期间,随着一次又一次金融问题的爆发,美国证券业经历了交易所自律、“蓝天法”约束、联邦证券法诞生这样一个监管愈加严密、越来越强调投资者保护和信息披露的过程。[40]从发行人角度看,公开发行是应发行融资需求的增加而兴起的;从投资者保护角度看,公开发行是解决非公开发行投资者保护不足的方案。而在已有公开发行制度的情况下,非公开发行又是满足交易费用减少,使证券融资行为利益最大化的方案。[41]
正因为如此,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在监管方面的重要差异体现在,前者通过法律制度设计强制发行人通过核准、注册等法定程序,并通过强制公开信息披露制度来尽可能消除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以及一般投资人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42]公开发行监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较高的发行成本和监管成本,一方面阻碍了企业融资便利,另一方面要求持续性投入监管资源。传统上,我们将获许投资者之类的制度作为破解保护投资者投资和便利私募发行的方案:[43]一方面,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向发行人要求信息披露、分析市场上的其他信息衍生新信息等自我努力的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在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监管资源更多地向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倾斜是更有效率的。
我们在评价此类制度时总是期望能够兼顾保护投资者和便利非公开发行,但如前所述,适用这一评价标准会遇到两种价值难以权衡的困境。这时可以参考保留非公开发行融资便利优势,并以其他制度(公开发行监管)弥补非公开发行投资者保护不足缺憾的思路,当需要在两个价值之间进行取舍时,将天平倾向于其中一种价值,并以其他制度来弥补另一端的缺憾。就此有两种方案:(1)以投资者保护为重点,严格限定特定对象范围。在提升融资便利方面,有两条路径,一是减少监管,二是简化注册程序和降低发行人获客成本。但如前所述,对公开发行进行监管的重要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减少监管与该方案侧重投资者保护的逻辑相悖,因此该方案下,宜通过第二条路径提升融资便利。(2)便利非公开发行,相对宽泛地界定特定对象范围。而对于被削弱的投资者保护,则通过其他途径弥补。
关于方案一,我国的审核制改注册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注册程序。但是,注册制并不当然意味着降低发行成本。在注册制下,中国证监会仍应保留部分实质性审核的权力,只不过发审的核心从片面关注发行人所发证券的市场前景的“商业判断”,转向发行行为本身的“合规判断”。[44]并且,注册制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在发行人获客成本方面,正常情况下,特定对象越稀缺,获客成本越高,而通过法律限制最高价格的方式来介入市场定价缺乏合理性基础。
关于方案二,通常来说,在有限范围内做二次筛选或者对一些特别对象加以特别关注,比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漏网之鱼要容易。SEC根据2012年JOBS法案,取消私募发行的公开劝诱禁止以便利私募发行,同时要求发行人采取合理步骤确认购买人资格并阻止某些“坏人”参与公开宣传的私募发行,[45]也是这种方案的具体体现。
这种情况下,与Ralston案对人数标准性质的认定类似,经相关标准筛选出的投资者大多数是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但这种标准是用于初步筛选的标准,其本质上并非定性标准。将其视为定性标准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这是一个基于现实不得不作出的次好选择,因为没有一个描述性的客观标准可以作为定性标准,相关标准是经验证明比较接近定性标准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一标准的缺陷可以借助其他途径来弥补。
总的来说,方案二的核心是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做加法。该方案下,关于改进发行对象判断标准问题转变为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强对特定对象的保护这一问题。
三、对特定对象的保护方案
经前文分析,我们并不需要过分追求一个能够同时描述金融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标准,金融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孰轻孰重也不那么重要,同时兼顾也很难做到。如果有其他途径保护某一标准不慎纳入的“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那么该标准可以被采用。
这个逻辑下,首先需要说明哪些投资者值得保护。我们应排除那些主观上自愿“不理性”地投资的投资者。这包括那些应当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却未能识别风险,或者已经识别风险但因主观原因过度冒险使其实际上不具有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特定对象获得了比其他参与者更多的投资机会,若一个堪堪符合财富标准的投资者愿意以所有财富博取更高投资回报的可能,那么其应该自负风险。这种风险或投资失败是由投资者的过度冒险带来的,与公开或非公开无关,因而不在“弥补”范围之内。市场经济下,对投资者的保护应关注如何引导投资者成为能动的自我保护者,[46]比如避免投资者遭受欺诈并尊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父爱式地限制投资决策以防止风险的发生。不过,如前所述,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划定这个范围,在个案中进行认定更具有可行性。
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财富标准和金融经验标准。
(一)重新审视财富标准
财富标准下,需要保护的是那些达到财富标准,但因金融经验不足,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关于具体的保护方案,由于发行行为主要涉及发行人、投资者和中介机构三方,故以下从这三个方面展开。又由于非公开发行的融资便利体现在对发行人监管的谦抑,因而,给发行人施加责任应是最劣后的选项。
从投资者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保护的手段有两类,一是行政手段,二是司法手段。围绕投资者进行的行政监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设置门槛,二是要求投资者更加审慎、理性地投资。关于前者,特定对象便是通过设置门槛来保护投资者的做法,但是,提高或降低门槛并不能解决投资者保护不足的问题。扩大特定对象范围带来的问题是那些不应投资高风险项目的投资者进行了不适宜的投资。这一问题无法依赖投资者自己解决。关于后者,给投资者施加义务意义不大。理性投资是一个主观的概念,难以客观化。如麦道夫事件所暴露的,尽职调查也可能流于形式,并不意味着投资是理性的。而且,在“理性投资,责任自负”原则下,我们不能也做不到要求投资者确实审慎投资。若遵循这条逻辑拟订法律方案,很可能又陷入逻辑怪圈。并且,要保证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保障其投资机会,应授予其权利而非施加义务。因此,通过加强行政监管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可行。
司法救济方面,由于非公开发行投资者保护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上,可以考虑在司法救济中给予投资者程序法上的优待。比如,简化知情权诉讼/仲裁的程序、调整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本文不主张在实体法上优待非公开发行投资者。主要原因在于,非公开发行的投资者承担更大风险,但拥有更高的收益可能,倘若这些总体上更富有、更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享有更多投资机会的同时却承担与其他投资者一样甚至更低的风险,显然不公平。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事后救济并不会有“正义迟到”的问题。对于非公开发行的投资者,我们期待其进行事前的审慎调查,其要进行理性投资,也应该在投资前充分评估投资风险。对于那些在发行时没有披露对于特定投资者而言属于决策所必需信息的项目,该投资者应该选择不予投资。外界的干预会破坏这一市场机制,我们要保护的也并非那些“懈怠”的投资者,如前文提到的,对于这类投资者的识别和救济,可以也应该留到司法裁判时进行处理。
不过,事后救济的有效性建立在投资者理性的前提上,其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的客观问题,仍然无法有效解决特定对象范围太大,纳入不具有理性决策能力的投资者的问题。经前文分析可知,这一问题无法通过投资者自身来解决。虽然这些投资者有一部分不值得保护,但我们很难在事前用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特定投资者是否值得保护,为避免“筛选失误”,减少事后救济的需求,也为避免“正义迟到”,可考虑引入更专业、更了解客户的中介机构。
中介机构是市场发展出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方案。其中,信息中介机构处理公众投资者缺乏风险分析能力的问题,金融中介机构隔断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更彻底地解决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信任问题并可实现规模化效果,节约社会资源。[47]引入中介机构能够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原因在于,对投资者而言,与发行人和所发行证券相关的信息可以依赖中介机构的专业能力去获取,其需要获取的关键信息变为与中介机构服务质量相关的信息,而获取后者比获取前者要容易,因为投资者向中介机构购买的是能力,能力可以通过既往评价(声誉)推断,而投资者希望从发行人处得到的是收益,收益面向未来,涉及财务信息、商业逻辑等专业领域,甚至没有同类产品可作比较,较难预测。此外,中介机构的介入,特别是自我保护能力弱的投资者经由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增加投资者的谈判地位,促使发行人自发降低投资者的风险。[48]对中介机构而言,相较于发行人和监管机构,其在“了解客户”方面有专业优势,更有能力引导投资者投资适宜的产品;由于其赚取的服务费是向投资者推荐优质投资产品的对价,与投资者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其有动力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最大化投资回报,据此提高声誉进而提高收费。可见,中介机构正适宜解决扩大特定对象范围带来的不应投资高风险项目的投资者进行了不适宜投资这一问题——可以由信息中介机构(如投资顾问)来协助识别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对于自我保护能力弱的投资者,要求其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进行投资。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按照前述逻辑,引入中介机构,特别是金融中介机构后,所有投资者都具有了“自我保护能力”,但考虑到中介机构介入交易会产生成本,本文仅主张将其作为扩大特定对象范围可能产生问题的弥补方案,并不据此否认特定对象标准乃至区分公开与非公开的意义。
关于分类方案,可参考《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由于主要的特定对象标准采用的仍然是财富标准,需要被特别保护的是缺乏经验的投资者,所以,在对投资者进行分类管理时,分类的标准应以金融经验为主。比如,具有一定年限投资经历/相关工作经历的投资者,以及金融资产达到一定规模的投资者属于自我保护能力强的投资者;金融资产低于阈值,且金融资产/所认购金额低于一定比例的投资者,属于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投资者,需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进行投资。
(二)重新审视金融经验标准
接下来以该逻辑审视金融经验标准。若如SEC那般,将金融经验作为独立的标准,可能“错误地”筛选出那些虽有金融经验,但相较于其投资,财富不足以承担风险的投资者。与财富标准语境下的情况类似,我们很难在事前用一个客观的标准衡量特定投资者的金融经验是否使其足以识别特定投资的风险。因而,依旧有进行投资者分类的必要。
分类方案方面,由于“特定对象”判断标准考虑的主要是金融经验,因此,在对投资者进行分类时,分类标准应为投资者的财富。比如,年收入或总资产达到一定金额的,属于自我保护能力强的投资者;资产规模低于阈值的,属于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投资者,对其最高投资金额和可投产品进行限制。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介介入,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中介机构应履行多大程度的注意义务,如何界定中介机构的责任等。但本部分要讨论的是是否有其他途径可以弥补非公开发行削弱的投资者保护,因此,该等问题暂不在讨论范围内。另外,由于适当性管理是现有的制度,对于相关问题,若有必要,可以基于现有框架进行调整,并非不可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将财富标准和金融经验标准作为独立的特定对象判断标准所带来的“筛选失误”有其他途径可以弥补。因此,我们在评价采取何种标准时无需要求标准同时解决投资者保护和融资便利问题。
结论
在不强求特定对象标准既要完美保护投资者,又要完美便利融资的情况下,特殊关系标准、财富标准和金融经验标准都是可行的标准,对于因放宽标准而不慎纳入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投资者,可要求其通过金融中介来投资,如此,也可以将合格投资者制度和适当性管理制度衔接起来。
具体方案上,不同于目前在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发行和公司债券发行时直接将发行环节和销售环节的要求等同起来的做法,在发行时,投资者择一满足特殊关系标准、财富标准或者金融经验标准即可,但同时,投资者所凭借成为特定对象的标准不同,其开展投资行为时的要求也有不同:(1)凭借特殊关系成为特定对象的,不对其附加更多要求;(2)同时符合财富标准和金融经验的,不对其附加更多要求;(3)对于凭借财富标准成为特定对象但金融经验不足的,需要通过金融中介进行投资;(4)对于凭借金融经验成为特定对象但财富未达到一定要求的,对其投资行为进行限制,比如对最高投资金额和可投产品进行限制。此外,在司法救济程序上宜更加便利特殊对象。
这一方案与前文讨论财富标准时提到的废除财富标准转而对投资者进行分类的方案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一方案不再纠结于财富和经验哪个更适合描述自我保护能力的问题,而是寻求一个综合性的方案来实现制度目的。
注释:
[1] 关于针对特定对象的公开发行制度的特殊性和监管逻辑,参见彭冰:《构建针对特定对象的公开发行制度》,载《法学》2006年第5期。
[2] 参见李有星、范俊浩:《非法集资中的不特定对象标准探析——证券私募视角的全新解读》,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5期。
[3]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上市公司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的公开发行所涉及的特定对象应当符合下列要求:(1)特定对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2)发行对象不超过三十五名。
[4]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21年修正)第四十二条规定,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包括:(1)公司股东;(2)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3)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所谓“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对于法人或合伙企业,细则仅设置了财富门槛;对于自然人,细则除要求达到财富门槛外,还要具有一定金融相关经验。
[5] 2021年《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向“专业投资者”发行;其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专业投资者的标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执行,目前,该规定指《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该办法要求专业投资者同时满足财富标准和金融经验标准。此外,《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比例超过百分之五的股东”可视同专业投资者。
[6] 根据该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2)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3)符合相关财富标准。但是,逻辑上,合格投资者定义要识别的就是那些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在实践操作方面,将“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作为条件之一意义不大。同样地,最低认购额要求其实也是财富能力的一种体现,因此,在此不将这两个内容作为一个具体标准看待。
[7] 修订前,要求满足特殊关系标准或财富标准;修订后,要求满足特殊关系标准,或满足财富标准的同时满足金融经验标准。
[8] See Regulation D Revisions; Exemption for Certain Employee Benefit Plans, Release No. 33-6683 (Jan. 16, 1987) [52 FR 3015 (Jan. 30, 1987)].
[9] 参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全国人大官方网站释义》,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xgwd/202003/P020200331823869638130.pdf,2022年3月6日访问。
[10] See Securities &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 Ralston Purina Co, 346 U.S. 119, 127 (1952).
[11] 参见彭冰:《投资型众筹的法律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页。
[12] 虽然2014年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排除了“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以及“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这两种情形,但是可以看到,事前“明知”依旧是主观方面问题,模糊性仍然存在。
[13] 参见李有星、范俊浩:《非法集资中的不特定对象标准探析——证券私募视角的全新解读》,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5期。
[14] See Transactions By an Issuer Deemed Not To Involve Any Public Offering, Release No. 33-5487 (Apr. 23, 1974) [39 FR 15261(May 2,1974)].
[15] See Exemption of Limited Offers and Sales by Qualified Issuers, Release No. 33-6180 (Jan. 17, 1980) [45 FR 6362 (Jan. 28, 1980)].
[16] SEC 2019对获许投资者定义进行的审查报告显示,2018年,投资者通过各种豁免筹集了大约2.9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在SEC注册的1.4万亿美元。此外,2018年,公司仅使用506(b)条款就获得了1.5万亿美元的豁免上市申请。此外,有研究显示,私募市场的发展与上市公司数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See Proposed rule, Release Nos. 33-10734(Dec.18, 2019) [17 CFR PARTS 230 and 240(Dec.18, 2019)].
[17] 从各国及地区的立法来看,投资者分类及判定标准主要包括:(1)投资者的“成熟度”,主要考量投资者的财经知识与经验、信息获取能力等;(2)投资者的财富水平,主要考虑投资者的资产规模、收入水平等;(3)与证券发行人的关系,主要考量投资者对发行人的了解程度、信息获取获许能力等。参见张宁等:上海证券交易所合作研究计划课题报告《合格投资者制度比较研究》,2010年1月,第21-23页。
[18] Howard M. Friedman, On Being Rich, Accredited, and Undiversified: The Lacunae in Contemporary Securities Regulation, 47 OKLA. L. REV. 291 (1994), pp.291-317; Syed Haq, Revisiting the Accredited Investor Standard, 5 MICH. Bus. & ENTREPRENEURIAL L. REV. 59 (2015), pp.59-80; Gregg Oguss, Should Size or Wealth Equal Sophisicadon in Federal Securies Laws?, 107 Nw. U. L. REv. 285 (2012), pp.285-320. Cited in Thomas M. Selman, Protecting Retail Investors: A New Exemption for Private Securities Offerings, 14 Va. L. & Bus. Rev. 41 (2020), p.41.
[19] Jennifer J. Johnson, Private Placements, A Regulatory Black Hole, 35 DEL. J. CORP. L. 151 (2010), p.153.
[20] Syed Haq, Revisiting the Accredited Investor Standard, 5 Mich. Bus. & Entrepreneurial L. Rev. 59(2015), pp. 70-71.
[21] Andrey D. Paviov & Susan M. Wachter, Systemic Risk and Market Institutions, 26 YALE J. ON REG. 445(2009), p. 452; So-Yeon Lee, Why the Accredited Investor Standard Fails the Average Investor, 31 Rev. Banking & Fin. L. 987 (2012), pp.990-992.
[22] Michael Ewens & Joan Farre-Mensa, The Deregulation of the Private Equity Markets and the Decline in IPOs , Natl Bureau of Econ.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6317, Sept. 2019.
[23] Howard M. Friedman, On Being Rich, Accredited, and Undiversified: The Lacunae in Contemporary Securities Regulation, 47 OKLA. L. REV. 291(1994), pp. 299-300.
[24] Section IV.B of the Report on the Review of the Definition of “Accredited Investor” (Dec. 18, 2015).
[25] So-Yeon Lee, Why the Accredited Investor Standard Fails the Average Investor, 31 Rev. Banking & Fin. L. 987(2012), pp. 992-995.
[26] Proposed rule, Release Nos. 33-10734(Dec.18, 2019) [17 CFR PARTS 230 and 240(Dec.18, 2019)].
[27] 参见彭冰:《投资型众筹的法律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页。
[28] Wallis K. Finger, Unsophisticated Wealth: Reconsidering the SECs Accredited Investor Definition under the 1933 Act, 86 Wash. U. L. Rev. 733 (2009), p.749.
[29] Stephen Choi, Regulating Investors Not Issuers: A Market-Based Proposal, 88 CAL. L. REV. 279 (2000), pp.280-301.
[30] C. Edward Fletcher III,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Under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DUKE L.J.1081(1988), pp.1149-1153.
[31] Thomas M. Selman, Protecting Retail Investors: A New Exemption for Private Securities Offerings, 14 Va. L. & Bus. Rev. 41 (2020), pp.41-63.
[32] 这里不考虑限额过低的情况。若所设置的投资限额过低,意味着投资者对损失的敏感性低,如此,公众都有风险承受能力,投资不再限于富人。但这个理论下,非公开发行类似于众筹,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33] Wallis K. Finger, Unsophisticated Wealth: Reconsidering the SECs Accredited Investor Definition under the 1933 Act, 86 Wash. U. L. Rev. 733 (2009), pp.733-767.
[34] Proposed rule, Release Nos. 33-10734(Dec.18, 2019)[17 CFR PARTS 230 and 240(Dec.18, 2019)].
[35] So-Yeon Lee, Why the Accredited Investor Standard Fails the Average Investor, 31 Rev. Banking & Fin. L. 987 (2012), p.1011.
[36] 假定“金融资产”能够代表投资经验,“个人年收入”也可以代表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只要择一满足“金融资产”或“个人年收入”条件即可意味着立法上并不要求投资者同时具有金融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
[37] Darian M. Ibrahim, Public Or Private Venture Capital, 94 Wash. L. Rev. 1137(2019), pp. 1161-1166.
[38] William W. Clayton, The Private Equity Negotiation Myth, 37 Yale J. on Reg. 67(2020), pp. 88-106.
[39]有研究显示,包括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在内的诸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都具有处置效应,这种情况影响成熟投资者的行为。Ryan Garvey & Anthony Murphy, Are Professional Traders Too Slow to Realize Their Losses?, 60 FIN. ANALYST J., 35(2004), pp. 35-43.
[40] 参见郭雳、郭励弘:《私募发行在美国证券市场中的地位》,载《产权导刊》2009年第8期。我国并非如此,但这是由于我国证券立法和私募实践较晚,并不影响私募存在的意义。
[41] 相关经济学理论基础,参见李有星:《中国证券非公开发行融资制度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42] 参见李有星:《中国证券非公开发行融资制度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18页。
[43] 参见梁清华:《论我国合格投资者法律制度的完善——从法定条件到操作标准》,载《证券市场导报》2015年2期。
[44] 参见蒋大兴:《隐退中的“权力型”证监会——注册制改革与证券监管权之重整》,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2期。
[45] 参见彭冰:《美国私募发行中公开劝诱禁止的取消》,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46] 参见洪艳蓉:《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7] 参见彭冰:《投资型众筹的法律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9、42-45页。
[48] Stephen Choi, Regulating Investors Not Issuers: A Market-Based Proposal, 88 CALIF. L. REV. 279(2000), pp. 290-295.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沙龙分享群。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点击下方链接保存课件。
点击下载金融科技大讲堂课件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为作者授权未央网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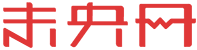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