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分享
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科技巨头们并没有像它们一开始所声称的那样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反而凭借着自己的垄断地位成为了矛盾和混乱的源头之一。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科技公司虽然积极与政府合作,但也不忘拓展自己的影响力。换句话说,政府在未来应该与这些科技公司保持浅层合作,并利用自身影响力约束这些公司,同时下大力气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本文译自Atlantic,原文标题What Big Tech Wants Out of the Pandemic.
早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前,科技行业就渴望证明自己对世界的不可或缺性。这些公司的高管喜欢把自己供职的公司描述为致力于“公共事业的公司”。他们的自我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理解:因为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确实认为自己创造的公司本质上是向善的,是世界所急需的。
然而,近年来,大众对这些公司的观感开始改变。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将它们视为虚假信息、制造矛盾和操纵生活的始作俑者,并注意到这些人类历史上最赚钱的公司的行为和它们声称的理想主义并不一致。
现在,对于科技公司来说,确认它们过去的使命感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疫情蔓延期间,Google Meet已成为学校的“替代选择”,而Amazon使人们可以不用去超市就能买到日常杂货。
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步履维艰,大型科技公司则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善良的朋友,愿意伸出有力的援手。正如Microsoft首席执行官Satya Nadella今年4月所写的那样,“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求企业和政府结成前所未有的联盟。”
同样在4月份,Google和Apple宣布它们将暂停竞争,与世界各国合作创建一个新的警报系统。它们将重新配置自己的移动操作系统,虽然设计上不兼容,但如果用户进入了COVID - 19患者所持设备的范围内,就会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这些公司最初的努力未能给一些公共卫生官员留下深刻印象,但它们仓促设计的计划可能会随着后续迭代而得到改善。通过记录你的社会联系和旅居历史,你的手机可以用来帮助证明你适合返回办公室或登机。
病毒的冲击压倒了各级政府。在面临大量失业申请的州,Amazon和Google已经介入,对陈旧的行政体系进行改造,以便在减少官僚摩擦的情况下促进资金流动。当Nadella提到建立新联盟的可能性时,他指的是远程医疗和虚拟学习的突然转变。公共卫生和教育可能是政府的传统职能,但Nadella建议,他所在的行业应该分担责任——“Microsoft将自己视为第一应对者和参与者。”
在这个奇怪的时代,网络经济带给了我们无可争辩的实惠,我们应该感恩。但这并不是对科技行业持怀疑态度的理由,因为该行业正试图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在病毒爆发前的几年里,批评人士开始预言,少数几家科技公司将很快变得比政府更强大。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以及操纵公众舆论和塑造市场的能力,将使它们能够不受阻碍地统治大多数人。
尽管这一警告很悲观,但它并没有完全抓住这些公司正在形成的战略——事实上,这些战略在疫情蔓延开始之前就已经形成——或者它们所构成的更严重的威胁。它们没有取代政府,而是在本质上寻求与政府合并。
科技公司的高管们并不总是渴望与政府合作。在多年的疯狂发展和政治不成熟期间,这些科技公司听起来就像青少年第一次遇到Ayn Rand一样。就像《Atlas》的主角John Galt一样,他们也抱怨政府的邪恶,以及它是如何压制伟大创新的。这种世界观带有利己主义的味道。Amazon、Google和Facebook等公司希望避免限制其老牌竞争对手的那种监管控制。
但如果利己主义与理想主义能够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时候,理想主义就是现实的。Google的共同创始人Sergey Brin,一个来自前苏联的难民,警告公司在其他国家开拓业务时可能产生的摩擦。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主义者,公司在其他国家经历最终说明了他的立场:尽管遵守了政府的指令,Google还是被黑客入侵,他们试图窃取其知识产权,并窥探一部分活跃人士的Gmail账户。
在整个行业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占主导地位——不仅仅是对威权政府的不信任。2016年,Apple拒绝了FBI破解一名已死恐怖分子iPhone密码的请求,这在当时引起了各方关注。Apple首席执行官Tim Cook在一封解释公司立场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认为,面对我们认为美国政府不自量力的问题,我们必须直言不讳。”
但随着理想主义公司的成长,它们开始重新考虑公司刚成立时的原则。大型科技公司也不能再像勇敢的创业公司那样令人信服。一场有左翼和右翼支持者的反垄断运动正在缓慢兴起。
当Facebook的Mark Zuckerberg于2018年在参议院作证时,他先发制人地承认,“我认为,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监管,而不是是否应该(监管)。”这一声明是对时代精神的承认。大型科技公司被指控传播虚假信息,从私人数据交易中牟取暴利,并导致青少年焦虑的上升。
Zuckerberg邀请政府监督企业,但并不是因为他受到了惩罚。在过去,当公众对大型企业产生怀疑时,这些企业就会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为了换取政府对其垄断地位的保护,这些企业将遵守国家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在1910年代,有远见的AT&T总裁Theodore Vail让他的公司接受了入侵性的监管。这使他得以几代人保持其统治地位。Zuckerberg也欢迎新规则,只要这些规则能对Facebook有利。Facebook确实在忙着让新制定的法规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去年,Facebook在游说上花费了大约1700万美元,比其他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要多。
Amazon将其第二个总部设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上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Google和Microsoft等公司与情报机构建立了关系更是与此脱不了干系。这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为政府提供有关如何升级其计算能力的建议。而有传言表明,科技公司之间最惨烈的内讧涉及到与国防部签订的一份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
随着疫情加速了大型科技公司对政府事务的参与,该行业最有实力的公司几乎肯定会利用它们与当局的关系,试图削弱实力较弱的竞争对手,获取利润丰厚的合同。不过,这些公司还将为它们在华盛顿的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从而增强政府的实力,无论好坏。
Donald Trump总统坚称,他对疫情的处理是成功的,但政府非常清楚自己的缺点之所在。它想要尽可能多地进行核酸检测,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它需要追踪接触者,但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足够有效的系统来处理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一种能力的光环来掩盖其徒劳的努力。由于疫苗还处于开发状态,政府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大型科技公司来弥补其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差距。
这种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令人担忧,但在特朗普时代却令人恐惧。这届政府对我们赖以立身的原则的重视程度很低,而且喜欢我行我素,不按常理出牌。我们也知道,一个由信息技术驱动的蔑视基本权利的当局可以做出何种事情来。
当然,美国离建立这样的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如此,过去的危机也可以被解读为如何充分利用焦虑和创伤气氛的教科书式案例。在9/11事件的一年前,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议通过强有力的立法限制企业使用在线数据,其中包括纠正(或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恐怖袭击打乱了美国的算盘。安全问题比其他问题更重要:国家迅速适应了无处不在的闭路电视摄像头、机场的全身扫描仪,以及权力急剧扩大到不透明的政府机构。
Shoshana Zuboff在她的作品《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中指出,正是这种氛围让Google和Facebook成为了强大的公司。恐怖袭击削弱了人们对隐私的担忧,为这些公司获取个人数据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恐惧催生了现在的反乌托邦现实。
非营利组织Privacy International称,现在至少有27个国家开始使用手机数据追踪冠状病毒的传播。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报道,超过24个国家的政府正在测试一款名为Fleming的软件,该软件是由以色列公司NSO开发的。NSO的参与不能激发信心。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指控该公司制造间谍软件,被各国用来监视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令人讨厌的异见人士,包括被谋杀的记者Jamal Khashoggi。
Google和Apple都不是NSO。它们还记得,2013年Edward Snowden曝光的那些与美国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合作的公司遭到了强烈抵制。它们并没有给政府它所渴望的确切数据,而是试图规定合作的条款,并以公民自由的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它们设计了COVID - 19预警系统,以防止数据的集中收集,并承诺该系统将随着疾病的消失而废止。(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不愿跟踪政府想要跟踪的所有内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想耗尽客户手机的电量。)随着时间的推移,Google和Apple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像关注使用它们地图的用户一样密切关注COVID - 19患者。
随着科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它们将面临进一步放纵自己最糟糕本能的诱惑。这两者都不是特别关注公民的隐私特权。以及,这两者都有一种不那么谦逊的感觉,那就是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公众的行为。甚至一些曾称赞Google和Apple系统的学者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300多名欧洲科学家和隐私学者签署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称:“我们担心,危机的一些‘解决方案’可能会逐渐走样,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实施前所未有的监控。”
如果没有新的约束,这个新兴联盟可能会变得比9/11之后出现的机构更加专横。在恐怖袭击之后的几十年里,智能手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它就像是一个储存敏感思想、偷拍照片和保存秘密的仓库。
因此,政府与强大的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只能保持浅层。美国政府应该效仿欧洲的数据保护机构,成立一个数据保护机构,有权审查这些公司如何利用流经其设备和平台的信息。政府不应将硅谷视为合作关系中的高级合作伙伴,而应利用其影响力暂停科技企业并购,为疫情之后的世界保留市场竞争的可能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这样的限制被认为是常识性的。两党在反垄断方面达成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Siemens、Krupp和IG Farben等德国企业集团的记忆之上的,这些企业曾欣然与当局携手,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对那一代人来说,垄断与其说是对消费者的威胁,不如说是对民主的威胁。他们相信,集中的经济权力和集中的政治权力的共生关系是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些警告也应该困扰后疫情时代世界和国家秩序的建设。如果在未来的世界,一个垄断公司与唯一比它更强大的力量联合,那么这个世界就算不是病态的,也绝不会是永远健康的。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沙龙分享群。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点击下方链接保存课件。
点击下载金融科技大讲堂课件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为作者授权未央网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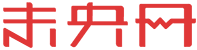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