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分享
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9月28日,全球贸易新常态与经济治理新框架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在圆桌讨论环节,鞠建东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在场嘉宾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第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新常态?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治理重要还是区域更重要?
第三个问题,在东亚中国能起带头作用吗?能够带头建立这个规则吗?行或不行?如果能的话,到底怎么做?
林毅夫:
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全球贸易新常态?首先来讲,从2008年到现在,贸易的增长速度,下滑了50%。那这段时间,持续这么长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这是一个新的状态,是肯定的。但是这个状态会不会持续?当然决定很多因素。包括我前面讲的,发达国家会不会进入到所谓新常态?如果说发达国家它的经济不能够恢复常态,那它贸易量一定会受影响,它的需求减少了,它的需求增长速度慢了。现在美国、欧洲加日本,到目前为止还占全世界GDP差不多一半,如果它的需求增长慢,贸易肯定受影响。
所以是不是会把这种新的状态,变成一种新的常态,相当大的决定,有前面在做阻止,包括里面所讲的。有没有办法找到出路?让发达国家真正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它能找到出路,进行结构性改革,那么它的经济增长恢复到从19世纪末到现在100多年时间里所表现的,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2%,经济增长大约是3%这个常态的话,那我觉得贸易就有可能恢复到常态,这是一个可能性。
但万一发达国家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有没有可能在中国作为领头龙,然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像东亚经济那么快速增长的话,那么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需求,会增加了很多。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即使没有办法完全替代,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下滑的压力应该也可以缓冲很多。那么这个缓冲,一方面是对全球贸易的增长有贡献。那么如果发达国家也能顺势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就是贸易增长,是过去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倍,可能还更高,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发达国家我前所讲的,全球基础设施,再加上我前面讲的,现在也提出来要帮助非洲跟其他低收入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倡议。如果这两个倡议都能够实行的话,那我觉得拜托目前国际贸易增长的缓慢,可以建立在全国经济比较好发展的基础上,恢复到过去,要不然很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点,中国应该是参加全球治理,还是只关心区域性的治理?我觉得中国人所讲得的是人。人的含义是什么?我感觉到的都是我,只要我能感觉到的,都是我的一部分。为什么说只要我能感觉到的,就是我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说身体是我的身体?因为人要打你你会痛,人家掐你你会叫,那是因为你感觉是你。
但是要是我感觉到的人受苦了,我也感觉受苦了,他快乐我也快乐。这跟我自己小我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竞速。他把我能感觉到的,都是我。但是儒家文化,这个我能感觉到的都是我,跟西方基督教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如家文化所讲的人,是以内心的感受作为基准的。而基督教文化里讲的博爱(中文翻译不太准确),它讲得是兄弟之爱,是教徒之间的爱。然后教徒之间的爱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没有亲属远近之分,因为它的关系都是经过上帝。然后他在教外就不是爱了,所以你看欧洲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教的冲突?因为你如果不是跟我同一个教,那就不是兄弟了,不是把你改变成跟我信成一个教,那就是冲突。
所以这是儒家文化跟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化很大差异点的地方,这个差异点,儒家文化的人有一个特性,是有亲属远近的,越近的感觉越强,越远的感觉就越弱。那么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当然追求全球治理,在这当中也会有亲属远近之分。
所以我们首先把自己的事搞好,再来把我们区域让大家都能共同和谐。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国家更远地区的人都和谐,所以它是全球治理。但是会有一个亲属远近,所以我们也会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开始,然后慢慢参与全球治理,改变全球治理。
第三个,中国能不能作为领头龙?我想很大程度决定我们自己的发展怎么样?如果我们自己发展好了,那么从我们自己的需要,比如说你要产业结构升级。那产业结构升级的话,我们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一方面需要国际市场,因为我们所谓开放的意思就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所以我们的产品会进入到国际市场,我们也会开发市场让国外的产品进来。
所谓两种资源,这里面自然资源,大家一般了解我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我们会利用国际的自然资源,给国际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创造市场。还有一方面,我们用国际技术,因为我们还在作为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后发优势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还可以利用国外的技术提升我们的技术。
那么相对来讲,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跟过去比相对丰富,但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所以我们也会吸引外资进来,这就是所谓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另外的话,比如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现在我们是叫比较优势,他就要转移到世界上去,那它就会变成给国外提供技术,要是作为外国直接投资,那就是资本出去。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中国的体量那么大,中国现在按照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经济增长率计算,即使现在下滑一点,即使每年6.5%以上,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是14%,也就是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将近1个百分点。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无非就是3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还是30%,如果你对世界增长贡献30%,其他发达国家没有第二个像中国贡献那么多,在那个状况之下,中国当然会是头部,中国当然会是领头龙。如果说中国经济下滑了,站在中方说,越往下你的带动就越小。
不过在各种场合里我也分析,应该讲说中国有条件、有可能性,在十三五规划期间,维持6.5%以上的增长。那么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应该成为世界领头龙应该是没问题的。
周皓:
林老师对三个问题都给了精彩的答案,我限于水平所限,只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际贸易有没有新常态,或者会不会成为新常态这种低迷的状态。那么我的答案前半句跟林老师是一样的,就是depends,后半句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depends什么东西。那么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者猜想就是,如果全球主要经济体还是依赖货币政策过渡的刺激经济,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国际贸易低迷的新常态不能走出来,但是如果2017年或者今后我们能够实现从纯粹依赖货币政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就能跳出这个低迷的国际贸易状态,这个新常态就要重新定位了。
那么我简单列举一下主要国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简单说一下,英国是肯定有的,脱欧之后,政府就说要避免英国经济出现衰退,一定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国际贸易,所以英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欧洲和日本在负利率实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基本上就是把银行中介给摧毁了,负的利率完全传递不到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上,所以现在的讨论也是央行的政策不是无限的,可能德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可能是将来唯一的让他们走出负利率、负增长的可能性。
那么美国,我们知道由于国会的限制,美国财政扩张开支的可能性是比较少的,但是今年的选举如果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民主党胜出,而且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其中一个,特别是参议院,如果从共和党转为民主党的话,美国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特别是你到美国去过,你坐过它的火车,开过它的公路,看过它的桥梁,你知道很多都是需要重新建的。所以美国也是潜在的有这种可能性的。
那么中国当然是更有可能,货币的超发,大家都经历了股市的泡沫,今天的房地产的泡沫,那么真正要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很可能不能再依赖过渡的货币政策,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未来能够把全球经济拉出低增长的低谷。我想这个和林老师谈的新结构主义的政策也是相吻合的,谢谢。
林毅夫:
这个我觉得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因为我们知道,政府可用的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更多的依赖货币政策而不依赖财政政策?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同意用财政政策,政府的投资可能会增加,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国家不愿意去用财政政策呢?关键的原因就是我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有很多人怀疑,就是说你用财政政策创造了就业,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可是你将来政府要还钱,如果你政府的投资不能够提高生产力,由将来的财政税收的增加来偿还现在的负债的话,将来不管是用货币增发造成的通货膨胀或者是直接增加家庭的税收,那么都是税收要增加。
那么既然如果将来税收要增加,我们知道家庭如果是一个理性的,它就要平滑消费,根据现在的消费定未来的消费。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一般政府增加财政政策直接去搞投资,一样创造投资需求,但是家庭呢,即使收入增加,消费需求也会下降,结果导致总需求会增加,那么只是政府的债不增加,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反对财政政策的原因。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出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做的时候,短期创造投资需求,创造就业。但从长期来看,必须提高投资增长率,如果它不是这么做的话,那么财政政策的效果也不高,将来有很大的可能也要造成货币的增发,跟现在采用货币政策的结果不太一样。
但是中国人不是讲嘛,思路决定出路,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009年,我在世行任上就提出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实际上讲的是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增加失业救济,也要财政赤字增加,这个是凯恩斯主义。
第二部分:基础设施投资。
但是它在发达国家做基础设施投资,更多的是挖个洞补个洞,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无非就是把旧的基础设施挖开,重新铺上去,效率提高不多。
发达国家有没有基础设施的平行,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非常有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的报告里面很高兴看到全球基础设施这个概念,现在越来越多人支持,因为只有这样子,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增加,它可能税收增加有点难,用货币化的方式也没关系,支持处于瓶颈状况的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者是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那么刚才周浩讲的这个效果就能够出现,不然的话,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结果都还是差不多的。
盛斌:
我简短地回应一下,一个是关于有没有新常态?我觉得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都说经济学家有两只手,好消息和坏消息。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新常态是发生。比如至少从贸易角度来讲,从贸易的结构、地区的结构,新的商业模式这个角度上,不用我多言,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新的状态的发生。
但是从速度上来讲,我觉得确实不好判断。这里面有周期性的原因,有结构性的原因。从周期性的原因上来讲,比如从偏宏观的角度来讲,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现在从需求侧刺激的手段和空间来讲,我觉得可能相对有限,甚至效率都不高。
对于很多国家来讲,从货币政策来讲,量化宽松政策,甚至负利率政策现在是无效的。哪怕有些投入新增流动性会用于偿还已经欠的债务,有些新增的流动性和贷款,并不能投资于实体经济,而是在资产市场上进行空转。
从财政政策上来讲,刚才林老师讲到李嘉图等价,另外欧洲的债务危机和中国地方债危,是这种公共债务高的国家,都认为持续的高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货币和财政这两个角度来讲,可能在短期当中,它的效率是有限的。
当然还有技术因素,从技术角度周期,我们也有一些选项,看到一些希望。特别现在我们讲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我叫物理空间,从生物空间、数字空间这三个角度进行创新,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长期的前景。哪些行业能够支撑我们未来的发展?
所以这种常态,要取决于我们定义常态的时间到底多少?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我斗胆说,可能10年算一个时期,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到危机之后,用了10年消化。80年代用了10年时间,美国和英国进行结构调整。所以10年当中,我觉得可能从速度上来讲,会存在很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另外从周期性因素之外,大家都讲到结构改革,比如这次G20当中,把结构改革作为未来的三架马车。但是结构改革需要发挥效力的时间会比较长,除了林老师刚才在他的主旨发言当中讲到,他会降低总需求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结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的难度大,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会很艰巨。
第二个问题,中国是重区域还是全球?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底气硬了,志在千里。那么全球经济治理,对于从贸易角度来讲,全球经济治理,我觉得重要还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要发挥自己的经验。从现在发展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未来全球经贸治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传统贸易。包括现在更加重视的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
第二方面:国内归置,贸易的新规则。
第三方面:投资,这次G20当中谈到9项非约束性的原则,为全球投资治理开创了一个先河。
第四方面:发展问题,特别与贸易有关的发展问题,除了林老师讲到的基础设施,还有贸易融资,中小企业等等。
这四个板块,我觉得未来是作为全球治理框架当中的基本内容,中国应该抓住自己有优势的部分。比如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带一路,通过项目推进,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进行推进。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领导权?我非常简单的说一下,可能未来中国也要根据不同所具有的优势和基础,我觉得可能在一段时间当中,美国可能仍然具有科技和金融的优势。俄罗斯安全是它的强项,中国还应该打经济牌,特别是贸易和投资。但是即使我们经济体量现在是第二,超过了美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国家,仍然在其他的方面也会考验中国,我觉得可能在四个方面,需要考验中国的能力:第一方面:必须具有新规则的能力。第二方面: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第三方面:管理和组织经贸联盟的能力。第四方面:维护世界上公正和道义的能力。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沙龙分享群。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点击下方链接保存课件。
点击下载金融科技大讲堂课件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本文为作者授权未央网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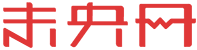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